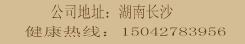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天敌 > 无肉不欢的世界我们应该吃肉么2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天敌 > 无肉不欢的世界我们应该吃肉么2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天敌 > 无肉不欢的世界我们应该吃肉么2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天敌 > 无肉不欢的世界我们应该吃肉么2
上一篇“肉类的营养”讲到了人类作为“异养生物”,肉食对于人类的营养价值、各种膳食元素的摄取,以及食肉及病害肉带来的危害等。结论是适量的肉类摄入是最理想的选择,适度的食物能量摄入比饮食结构还重要。第二篇讨论了肉类饮食对人类进化过程的影响。人类对肉食的回避、禁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类对肉食的索求似乎吃掉了地球上很多动物物种,尽管这是有争议的假说。
第二篇人类进化中的肉类
发现于年的法国南部的Chauvet洞穴上的巨型动物木炭画,约绘制于3万多年前:这些精确且动态的画,说明我们的祖先花了很多时间观察他们捕获的动物。图片来自于网络。
食肉属于我们人类的进化遗产,这遗产还包括巨大的大脑(事实上大脑长这么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吃肉)、直立行走和符号语言:这是一种事实陈述,并不是为了给这本讲食肉的书开个头的牵强附会。
食肉的起源——出现的动机、获取肉类的方式、吃掉的不同物种的相对量——都无法从稀疏的化石记录里理出头绪。
前农业时代的新石器狩猎社会,还不能狩猎巨型动物,其肉类消费量无法从相对丰富的考古中去了解,因为吃小型动物不会留下确凿的痕迹。单分析人骨胶原中的氮的稳定同位素,已经明明白白地证实,那个时代的饮食中,含有少量或大量的动物性食物。
许多农业社会里,肉类消费逐渐或偶然降到了非常低的的水平,无论是因为传统耕作方法的生产力低下,一些地区产出的增长跟不上人口密度的升高,还是出于宗教动机而禁止吃肉,还是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周期性的食物短缺和饥荒。在大多数文化里,肉都是人人垂涎的食物,对肉类的强烈渴望贯穿了整条历史长河,跨越了所有的经济阶层。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吃肉的机会一旦增多,人均肉类消费量就开始上升,首先是在19世纪的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趋势在20世纪变成了大规模的全球饮食变迁,一些西方国家的肉类消费达到饱和。
一、猎取野生动物——人类进化史上的肉类
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早的人类的95%以上都是以采食为生,采集各种可食用的植物,收集昆虫和陆生及水生的无脊椎动物,诱捕或直接抓小型哺乳动物,并使用工具去猎取大型的食草动物,以及抓鱼和水栖哺乳动物。
毫无疑问,食肉在人类的身体和行为进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人类大量吃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出于什么原因开始,这些我们都只能去猜测。古人类全都是杂食性的,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他们的狩猎技能,对普遍肉类消费水平有决定性的影响,热带雨林的比率最低,而草原上的最高。
狩猎为人们提供额外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非常受欢迎。这些狩猎活动所获得的肉类、内脏和脂肪,不仅大大地促进了古人类的身体进化(尤其是使他们的胃肠道变小,并使他们的脑量非常大),更为古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毫无争议地,肉类是构成我们的进化遗产的关键要素之一。
虽然现代西方市场上能买到的肉,主要是少数几种哺乳动物和禽类,但历史上和全球范围内,食肉的种类一直都很丰富,简直无所不包:各种体型的生物(从蛆虫到猛犸象)和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都被手机来杀掉或吃掉。刚果的野味市场就有烤好的几近灭绝的山地大猩猩和黑猩猩肉售卖。
01灵长类和古人类
对黑猩猩的捕猎的观察结果表明,它们会互相合作吗,随后成功的雄性黑猩猩会把肉分掉,这些做法增加了个体黑猩猩得到肉中所含的优质蛋白和必需的微量元素的机会。而且,分食肉也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而且雄性长期依赖都用肉做交易,来换取性行为。灵长类动物的捕猎行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进化史上出现的类似特征,因为离我们最近的灵长类祖先也是杂食动物。
古人类和早期人类是杂食性动物,没有哪位采食者会忽略动物性食品,尤其是生活在半干旱或者北方气候下,生存环境受季节变动影响很大的人群,更不可能忽略了。
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约万年前肉食的食用呈增长趋势,最后,对肉的采集从背大型食肉动物杀死的猎物身上捡拾,开始扩展到有意的狩猎。
但食肉的深远影响,远不止于替代植物性食品,为人类提供优质的营养。斯坦福(Stanford)通过对黑猩猩的观察,把人类智力的起源与肉联系在了一起,这并不是因为营养品质提升,而是因为在集体内分享肉是有策略的,需要认知能力不断提升。当灵长类和早期的古人类的平均脑化指数(实际脑量/体重对应的预期脑量)在2~3.5的时候,人类的值略高于6。万年前,南方古猿阿法种的脑容量低于立方厘米,万年前直立人几乎是其两倍大,而且成年智人的大脑比直立人还要大50%。
大脑增大了很多,代谢值非常高,但是整体基础代谢率并没有相应升高,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达到那么高的代谢值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艾洛和惠勒提出了高耗能组织假说,把大脑增长和肉类消费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02新石器时代的肉类消费
智人最早出现在190年前的非洲,其早期的狩猎能力,并不比他们的先辈更加高明。有了射程更远的武器之后,猎杀较大的哺乳动物才称为可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饮食是动植物混搭。
只吃植物蛋白的人,其δ15N(氮稳定同位素)值与同一地区食草动物的值相同;而那些值吃食草动物蛋白的人,其δ15N值等于当地食草动物的值再加上3%~6%的富集值;而吃混合蛋白的人,会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形成一种线性的富集比率。这种同位素证据表明了富集的存在,因此每个针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骨胶原研究,都证明了有肉类消费的存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食草动物的肉是欧洲大部分地区饮食的重要成分,但重要的转变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因为饮食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水生生物的消费逐渐增多。
芬奇(Finch)和斯坦福(Stanford)认为,狩猎社会的饮食趋向于经常食用肥肉,这个趋势是由“肉适应性”基因选择导致的,这些基因让人能抵抗食肉相关的风险,同时延长了经常吃肉之人的寿命。旧石器时代的肉食,因烹调(烧、烤、熏)的普及而变得更容易消化、更美味,也更安全。烹饪的发明和应用,对人类进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假说认为:人类对大型食草动物的肥肉的索求,有可能是更新世晚期巨型动物相对迅速灭绝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主要原因。
03更新世晚期的巨型动物灭绝
用来描述更新世晚期的生物灭绝时(更新世结束于年前),巨型动物这个词不光指猛犸象和其他大型的食草动物,还指一切成年后体重超过40~50千克的哺乳动物,也就是一头幼鹿的体重。
巨大的食草动物成为人们中意的狩猎对象,不仅是因为猎杀后回报丰厚,会得到大量的肉(产出的食物能量是花在捕猎上的很多倍),更是因为它们富含脂肪,比小型的动物药多得多,它们的能量密度可能是那种只有几千克重的动物的两倍。
猛犸象复原图,图片来自网络
20世纪50年代晚期,欧文的狩猎导致灭绝的假说开始在当代复兴。随着马丁(Martin)论文的发表,这个假说在接下来的50年里都流传不绝。观察特定地区的个别物种,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在欧亚大陆和澳洲,有些大型物种早在更新世晚期之前就灭绝了(直牙象),别的物种生存则因气候变化的压力重重。此外,一些大型食草动物,包括那些堪称完美狩猎目标的动物,存活到了全新世。所以,50多年过去了,马丁掀起的灭绝之争,对于巨型动物消失的原因仍未真正达成一致。不过现代主流的看法,都认为那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单纯是由食肉的猎人们的捕杀而导致的。气候变化及相继而来的植被变化似乎是关键因素,人类活动也起了一定作用,主要是选择性狩猎和人为火灾。
04不同生态系统里的狩猎
决定动物量密度的最为根本的变量,乃是克进行狩猎的潜力,也就是不同营养级之间能量转化的量级。
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对于讲求高回报的狩猎行动来说,环境条件比较差。热带雨林里使用弓箭的猎人,狩猎成功的概率,比他们在开阔树林或草原上的同行低很多。而捕获的小型动物的肉类所能提供的能量,只是追逐时投入的能量的两三倍,还有很多狩猎会空手而归。
由于在动物量丰富的环境下有很多狩猎机会,所以猎物的平均体重就成了选择目标的关键因素。最常见的猎物,是那种体重适当、生育能力相对较高、该地区种群密度大的动物。
野猪繁殖很快,成年后体重可达90千克,在热带和温带环境下都是人们喜爱的猎物;鹿和羚羊也一样,它们最小的体重不足25千克,最大的则超过千克。但是最理想的猎物时大型的有蹄类,不仅是因为蹄子上含有大量的肉,更是因为它们的脂肪含量比寻常肉类高。
一些体型小但脂肪多,生活在地下的哺乳动物,包括蚁熊和豪猪,是仅有的例外。野生肉类很瘦,这就解释了为何就算有充足的小型食草动物,猎人们还是对吃食物能量密度高的肉类充满热情。长时间只吃瘦肉,一点其他食物都没有的话,会引起急性的营养不良,这叫兔肉综合症(rabbitstarvation),它会引起恶心、腹泻,最终导致死亡。
以陆生大型食草动物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猎人,或者北极地区那些几乎完全靠吃富含脂肪的海洋哺乳动物生存的人群,都不会有微量元素缺乏的问题。因为他们也吃被杀动物的内脏,内脏于肌肉相比,富含维生素C、D和E,还富含核黄素、烟酸、B12、叶酸和铁。野生动物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于家养的动物,这个事实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大量食肉的猎人为何没有动脉硬化的问题。
肉类供应也需要写作和分享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肉类分享很明显一直是人类写作进化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05定居社会的野生肉类
人类社会逐渐转变为定居社会,规律地进行作物种植,这肯定是个渐进的过程。在早期的定居农业社会里,普遍的采食和特定的狩猎仍旧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古埃及和中国历史早期,这些最古老的冲积文明里,狩猎依然是普遍的做法——在埃及,猎获的物种包括鸭、鹅、羚羊、野猪、鳄鱼和大象;在中国,猎获的物种从野猪到大象不一而足——而在欧洲,这一直是对以植物为主的饮食的补充。
在热带非洲的绝大多数地方,有蹄类动物和啮齿动物正在以空前的速度遭猎杀。中国的情况与之类似,一方面是因为传统上偏好吃外来物种,另一方面收入增长,让数百万的消费者能吃得起这些美味,他们通常是在铺张的宴席上吃。
牛肉,图片来自于网络
二、传统社会——动物、饮食与限制
沿袭了长期以来的采食生活的传统(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1)牧民社会;(2)流动耕作的农民社会;(3)永久定居的农民社会。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绝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口粮中,肉类的含量微乎其微,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族群,其饮食里基本没有肉。野生动物的边缘化,是农业扩张无可避免的结果。小规模的季节性狩猎和偶尔的不做活动,在年消费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人们循化大型动物——牛、水牛、牦牛、马和骆驼——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作为肉的来源,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动力源,为耕田、食物加工、道路及越野运输还有战争提供畜力。
此外,很多社会,肉类——各个种类或者某些特定的品种——成了禁物。但这些禁令,虽然有的维持了上千年,也不能革除食肉这种普遍的愿望,不能推翻肉类在食物中享有的崇高地位:不受限制地吃肉(形式多样,从大快朵颐到精心准备的筵席),是统治者和富裕的地主们,以及后来的富有的市民们明显的特权之一。
01动物驯化
里彻辛(Richerson)等人的说法具有说服力:农业在旧石器时代是不可能之事;但在新石器时代是不得已之事。年前并没有驯养动物,不过,只用了几百年就成功驯化四种最重要的肉用物种。
大约在年前,山羊和绵羊最先被驯服,接下来是猪(10年前)和牛(年前)。马的驯化迟至2年前。
水牛很可能是在公元前年左右的印度和中国驯化的;驴的驯养最初是在埃及(公元前0年);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分别来自阿拉伯和伊朗东部地区,最早驯养是在公元前年左右;牦牛来自中国的西藏高原(约公元前0年);无峰驼(公元前3年)和羊驼是来自安第斯山脉的野生原驼的后代。这些物种全都可以吃,但是他们的驯化,首先不是作为肉食动物,其更重要的用途是驮运、耕地、取粪肥、挤奶喝剪毛;当然,狗应当是驯养的动物中最著名的一类。
反刍动物都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它们能消化易大量获取的纤维组织,而其他动物不能代谢纤维;它们还生产优质的、富含蛋白的乳类喝肉类(以及血)食物,让牧民能够在贫瘠的、无法种植作物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也能让定居的农民的饮食种类更丰富。
杂食性的猪,在欧亚大陆(除了印度)上到处可见,还有另一种优势:其基础代谢率比山羊、绵羊或者牛都低,因此能更为高效地吧饲料转化成肌肉喝脂肪。
鸭的驯化最早是在年前的中国。鹅的最初驯化最可能是在公元前0年的我埃及。
02人口密度和环境制约
农业的兴起(以及后来的集约化)首先是对食物需求增大的一种回应——食物需求增大是由人口的升高导致的,通过比较所有重要的人类生活的承载能力,可以更好滴说明这一点。采食性的人口密度最低,开采区的数量是1人/平方公里;季节性干旱地区为10人/平方公里;沿海捕鱼并猎杀海洋哺乳动物的群体,人口密度接近1人/平方公里;牧民草原地区为1~2人/平方公里;农民把耕地上密度提高到人/平方公里(1~2人/公顷)。
之所有能有这么高的人口密度,不仅是因为集约化的种植,更是因为饮食中几乎没有肉,尽管大量家畜和家禽的存在很普遍。
传统社会里,陆地上没有可移动的无生命的动力源:只有两种机械装置能转化水流和风的能量——水车和风车——它们都是固定在外,而且沉重、相当低效。
驯化的大型动物可用来完成运输和耕田、食物加工等诸多的机械性工作,从而帮助当地进行采掘或生产。和马比起来,用速度较慢但饲养要求没那么高的反刍动物来承担这些工作的成本较低,因此牛一直是重要的役畜。马主要用来骑行和打仗。因此,体型大、繁重缓慢的役畜变得非常宝贵,不会被轻易杀掉吃肉。
此外,在没有合成的无机肥料的情况下,所有的动物都是丰富的肥料源,其中的氮化合物相对富集。动物粪便里的氮含量通常在2%以上,尤其是猪粪和家禽的粪,氮含量超过3%。
猪,这种出类拔萃的杂食动物,可喂以食物加工费料、农场或家庭垃圾。
很多考古学证据和文字记录,都证明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饮食中,肉类含量都很少。
03肉类摄入量的长期停滞期
古希腊历史记录让我们对神话里食肉的英雄们印象深刻,但希腊和罗马的饮食,却是以谷类和豆类为主的。在罗马,肉类被视为祭祀经济的最好产品,薰腌过的肉类是罗马军队的必备食物,但总体的消费量很低。随着人口密度的缓慢增长,平均饮食的品质也有所下降。
饮食品质上的变化,体现在定居人口缩小的身材上。整个罗马帝国时代,男性和女性的身高都没有增加,而且从地中海地区移居到欧洲中部的罗马移民,比当地人口平均低4厘米。
直到18世纪80年代,西欧才开始客服高死亡率,战胜饥饿。
20世纪20年代,中国河北省,每年的肉类摄入量低于1.7千克/家,或者不足克/年/人。这意味着在中国贫穷干旱的北方省份,大多数农民只能吃上几口肉,一年也就两三次,通常是在过年或者婚礼上。在最富裕的省份,肉类的消费则大大增加,江苏省的最大值超过了30千克/家(或大约5千克/人)。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人均食物能量摄入量中,肉类提供的能量只占2%一左右(与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情况相似),或只相当于白薯的一半,还不到豆类的1/3(主要是大豆),豆类是中国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04回避、禁忌和禁令
即使是对食物不挑剔的传统猎人,也会有所选择,他们不会把从周围环境里收集、诱捕或猎杀而来的各种肉类都吃掉。猎人通常不去吃的那些动物,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不适合食用,还会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从能量回报相对于追逐的风险来说太低,崇拜或厌恶特定的物种,认为其神圣、不洁或者恶心等。
这种文化驱动的回避现象,已经演化出两条主线:作为非正式的禁忌和作为正式的禁令。
特定的禁忌——不管它们是特定文化下所有人都要始终遵守的禁忌,还是只有某些成员需要遵守,抑或只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遵守的禁忌,都可见于每一种文化中。中国人的孕期禁忌尤为复杂。
最著名的出于宗教动机禁止吃某些食物的例子,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不吃猪肉,印度教不吃牛肉,还有按照佛教最严格的阐释,不能吃肉。
日本天皇颁发禁食肉诏,第一次是在公园年,也就是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的一百多年之后。年,政府宣布吃肉对健康很重要,一年后,一份官方公告公布天皇经常吃肉。年,日本全国的年人均肉类供应量也只达到克/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依然从没吃过牛。到年,均值上升到大约1.7千克。而在年,是2千克/人,依旧是微不足道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
最强大的一条禁令是北美避食马肉。
05肉——久负盛名的食物
在我们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肉一直都是地位显赫的食物。那些能够获取很多肉的圈子,在慢慢地变化。自古代以来,统治者就一直是肉食者。中世纪时,经常吃肉(以及内陆地区吃海产)的圈子,扩大到了几个阶层:贵族、上层神职人员、富裕的商人和富有城市居民,通常把吃肉作为炫耀性的消费。
作者简介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从事能源、环境和人口变化、食物生产及营养、技术创新、风险评估和公共政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他已经出版了30多本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斯米尔是曼尼托巴大学特聘的荣誉退休教授,加拿大皇家学院(科学院)研究员,第一个被美国科学促进会授予科学和技术公众普及奖的非美籍学者。
1年,斯米尔入选《国外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思想家50强。著有《材料简史及材料未来》《美国制造》《收割生物圈》等畅销书书。
译者:王洁,曾在中国农大学生物、协和医学院学药理,现为健康产业行业分析师。
声明:本文为读书笔记,所以大部分内容为书摘。作者及译者如有异议,请留言告知。
迂子爷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jj/85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