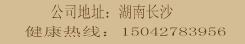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当我们登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当我们登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当我们登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当我们登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山洞的入口,天空是被拘束的狭窄一隅。
今天文章的主角,是一对热爱山野的户外组合:可乐与腰子。可乐带来了两个小故事,里面有着他们对登山的顿悟,期间混杂着遇到的困惑与烦恼。这些只能在行山中感受的思绪,可能是所有山友迷恋户外的意义所在。
肾上腺素峰
十三陵往北的山里,我和腰子几乎同时看到半山岩缝的洞口。年的万圣节,我们带上装备前往那个不知名的山洞,第二天攀登了一座不知名的山峰,腰子称之为“肾上腺素”。
山洞里,腰子摸着头顶干燥的岩石,手电的光照出深邃的侧影,洞口在我们头顶,星星已经爬满天空,树的剪影和山一样生硬。很难想象城市就在那座世代不变的山外,那座庞大到无边际的城市,甚至在地球上空也能看见,嚼碎人,吐出雾霾,追逐闪耀着灯红酒绿的繁华,无关山洞的喧嚣。
我们分别钻进各自的睡袋,这里的空气干燥舒适,头灯照亮了飞舞的尘埃,不过干净清晰。
“你说,洞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问腰子,光无法涉猎更深处的地方,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周安静得可怕,我们并不想深入。
“管他妈的。”腰子打开了一罐北冰洋,仰头喝了一大口,摘下手套,开始剥夏威夷果。
“要是有什么东西我也认了,藏这么久不出来,认了。”腰子笑了,嚼着夏威夷果。我也笑了,说那我也认。
我躺了下来,防潮垫的充气枕头落满了灰,不过这丝毫没有关系——
这儿的一切都那么干净,不是城市肮脏之中刻意营造的那种干净。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逃离学校,穿上冲锋衣带上刀,逃离抱着书本和寻欢作乐的人群,来到这个偶然发现的山洞,置身这刻意营造的自由。
腰子打开了一袋儿巴旦木,我告诉他连壳儿一起吃的新吃法。他很快采纳,椒盐和奶油的味道深入巴旦木的壳,连着果仁的油脂味丰富口感,再配上北冰洋对舌尖味蕾的刺激。这种体验只有山洞能带来,无论课桌上,餐桌上,还是柔软舒适的床上都不能。
我调亮了头灯,摸出背包里的书。背包像个忠诚的伙伴靠在我身后,阻挡着寒冷和黑暗,我热爱我的背包,就算这个世界抛弃了你,背包也会永远等待着你的下次出发,背负系统的每一寸织带都像是拥抱。
腰子说可以理解,正如他对自己弓箭的感情。
梭罗写的《荒野孤舟》有精美的封面,不过却不适合大声朗读,我厌倦了学院气质的软弱哲思,让人想起卢梭漫步的羸弱白皙。于是我扔开这本乏味却标识荒野的书,打开了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给腰子分享名言警句。
“凯鲁亚克有次独自来到海滩,在星空下生起一堆火,煮罐头里的豆子猪肉,烤小香肠,就着葡萄酒吃,虽然香肠沾满了沙子,不过这逼说真特么好吃。”豆子猪肉激发了我的食欲,想象起了滋滋作响的油。
腰子也提起了兴致,他说背包里还有香肠,不过是明天探路的给养,所以我们只能说说而已。
沾满沙子的香肠让我想起了某个在水边露营的清晨,我看着太阳一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升起,一边用炉头套锅煮泡面,腰子抱怨着蚂蚁爬满了草莓酱夹心面包,我们昨晚忘了把食物挂在树上。他给我看爬满了蚂蚁的面包,然后耸耸肩,连着蚂蚁把面包塞进了嘴里。
毕竟,一切蛋白质都是宝贵的。
我继续翻书,读出另外一段书中的精华:“不管是哪所大学,只要有血有肉的人出现,就都会被视为异类。事实上,大学不过是为培训没有鲜明面目的中产阶级而设的学校吧。”
腰子深以为然,他热爱的生活是二胡,哲学和弓箭,他总说大学是自我教育,其他“西装的事”都是狗屁,“一群小娃儿,玩儿点大人游戏,满手沾着肮脏,还觉得是巧克力。”
“所有这些人,蹲的都是白色的磁砖马桶,拉的都是又大又臭的大便,就像山里的熊大便一样,但他们在用水把大便冲走以后,就当成自己完全没有拉过大便这回事,而没有意识到,大海里的粪便和浮渣,其实就是他们生命的源头。”
我指出书中划满红线的一段,腰子说:“人总是试图用文明来伪装,其实永远摆脱不了自然的本性。”他戴上针织套帽,把抓绒内壳垫在头下,舒服地躺在睡袋里。
“大海里的粪便和浮渣。”腰子的声音渐渐变低,就像舞台上渐弱的音效。
“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腰子关掉了头灯,没有网络的生活让人容易犯困。
可能是为了文明带来的虚妄安全感,我们把一支手电留在洞口彻夜明亮,淡黄色的光让我觉得很安心,我把抓绒套在脖子上,像腰子一样戴上帽子,感觉自己就像裹在蛹里的虫,我用冲锋衣盖住脸,构建封闭舒适的空间,只留下呼吸的缝隙,这让我想起了童年一个人睡时对黑夜的恐惧,把自己埋在被子里,似乎就隔绝了所有妖魔鬼怪。
我把刀塞进睡袋里触手可及的地方,武器就像一个男人的标志。在入手冷钢直刀之前,每次夜训时,腰子都会带上那把“十分趁手,合适得一逼”的钢棍,那是去年夏天时我们某次废墟探险中的意外收获,他用伞绳把钢棍的手柄细细包好,细心地放在副包里。
不过我们至今没有遇到需要使用武器的危险,只是吃烤翅时,用刀确实比用手方便。
那个夜晚我睡得很香,我记得做了个清晰真实的梦,我梦见白色的光芒照亮了洞穴,洞穴像是巨人吞吐的胃,吸入洞外飞速旋转的一切,只留下白色的虚空。
世界是匆匆搭建的布景,为的是让我们相信其真实。
我在破晓时分醒来,思考身处何时何地,眼前的景色在一瞬间轮廓分明,世界就像匆匆搭建的布景,为的是让我们相信其真实。
腰子也醒了,他把手伸出睡袋,触碰青白色花纹的岩石裂缝,这座山心脏的膜壁。
“湿度,温度,纹理,这些都是可以模仿的。”他的口吻总让我想起游戏里的普莱斯队长。
“你真的无法证明你不是培养皿里的大脑。”
腰子上一次说这话时,我们在足球场上写着“禁止攀登”的高台上吃烤羊腿,天空是雾霾之后罕见的蓝色,像萃取后的海被涂抹在白纸一样的天空,“程序代码冲击着操场,头上是天空还是宏世界的电脑桌面?”腰子点着烟指向太阳,我们都是在《科幻世界》的毒害中长大的一代。
洞口的风吹动陈旧的树,枯黄的叶铺满潮湿的泥土荒野,我们几乎在同时看到了那座不知名的山,褐黄色的岩石突兀破碎地生长,深灰色和金黄色的灌木从森林的边缘一路延续,更高的地方,一颗墨绿色的松树趾高气扬,数十只黑色的乌鸦在山顶的空域盘旋。
“去看看山顶有什么,怎么样?”腰子给自己上了支烟,他说为了心爱的姑娘曾经戒烟四年,后来不爱了。
“没路。”我开始戴护膝,口是心非般地漫不经心。
“干,我们就是路。”腰子教官把灯具打包扔在洞口,爬山需要尽量减轻负重。
于是,就这么决定了,我们走入初冬萧瑟的森林,灰白色的生硬灌木划破皮肤带来的原始刺痛感,踩断脆弱枝木的清脆声在山谷中回荡。谷地平坦的边缘,干涸的水涧堆满巨大长满青苔的山石,更为高大茂密的植被生长得密不透风,那座不知名的山就在跟前。
前方的道路很难开辟,长满了烦人的野枣树,它们有干瘪苦涩的果实和满身的刺,我称它们为“山婊”,长在每一座山上,尖刺可以穿透手套,果实鲜红而空心。
我们仰头能看见山峰,和那棵诡异壮烈的松树,乌鸦一如既往地聚集,鸣声悲伤邪恶。
山体无数块褐黄色的巨型页岩横亘,石缝和灌木之间,约八十度的倾角,腰子说,这应该是条上山顶的捷径。
我们开始了攀登,松动的页岩会碎裂着掉落,但层次分明的沟壑也便于找到支点,腰子教官触碰到岩壁的一瞬间起就像只猴子,我看着他手脚并用熟练地爬升,岩壁就像预先设计的阶梯,然后他安逸地坐在平台上指挥着我寻找支点。
“伸展你的四肢,找到支点,收点,撑跳。”他的指挥只能是概略性的,毕竟只有我自己指尖的摸索,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支撑。
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人只有信任自己的身体才能抓住岩石的凸起,手臂的每一块肌肉,他们在健身房的镜子里和在山的注视里,是截然不同的感应。我感受到手臂和腿的语言,它们告诉我可以将力量注入山石,肺部平稳的呼吸也给我信号,这只是无数游戏中的一种。只有在与山的亲密接触中,你才能感受到力量,也更加对羸弱嗤之以鼻。
腰子用标准的四川话喊话:
“往上耸,不要虚,你觉得不行的时候,肾上腺素会解决一切问题。”
肾上腺素会在你失去平衡时让你下意识地抓住植物的根,也会在你找不到路时激发走下去的野性,在你踩空时赐予双手扎根山石的力量,在你心灰意冷时消除头脑中叫喊的放弃。
如果人渴望感受思维与身体的离间感,置身陌生的山野最为清晰,身体的反应会给意识鼓舞,思想的兴奋会让身体运转积极,这是奇妙互补的化学反应。
当我们站在山顶时,已经耗去整个上午。凛冽的风吹散了寒鸦,我们看到了更远更瑰丽的山,波浪般翻滚的峰群,没有循规蹈矩的游人,也没有挺着肥肚子拄着双登山杖的所谓驴友,我们在陌生的山峰顶端吹着陌生的风。
“没路下去。”我调整着护膝,峰顶周围的峭壁充满绝望的诱惑,也写满自由。
“反正不走回头路。”腰子留下了空烟盒作为纪念,我们对表确定时间,太阳落山还早。
“就这样玩儿呗。”我看着更远处的群山。
“我们就是路,剩下的……”腰子戴上墨镜,阳光有些刺眼,和雾霾一样沉重。
“交给肾上腺素。”
平淡日子里的刺
85号店的老板热情地抬出装满香烟的纸箱,慷慨地抬手任人挑选,腰子只是扫了一眼,就在花花世界中挑出心仪的香烟,信手拈来,这个成语是形容买烟的。
我刷了瓶可乐,无糖,只有和腰子一起例训时我才喝可乐,这种饮料本质上是不健康的,工业流水线上廉价的消耗品,黑色的液体容易让人想起粗糙的烟囱,燃烧的石油,荒废工厂里的铁锈齿轮,或者北京的天,反正没一样好东西。
不过可乐于我却意义非凡:在海坨山,42斤重装登上销魂坡时,站在白雾弥漫的垭口,我打开了背包深处的可乐,致敬雷雨和松林,一口,终生难忘;白河峡谷的最后一日,徒步三天的我们终于搭上了返程的车,带着满身疲惫,抱着背包,就像抱着战友,可乐流过干哑的喉咙,像他妈在歌唱;开辟落水涧新线路,九个小时的穿野,当那片天堂一样的枯黄草原和远方的山一起出现时,我挑着满身的野枣刺,只有一个念头:
“是时候喝可乐了。”
所以腰子说,既然你每次都带着可乐出发,以后就叫可乐吧。
我说,那你背包里,有几个腰子?
腰子纠正我的用词,他说,腰子也是需要尊重的,应该叫肾。
我们走出85号店,浓郁的黑夜,雾霾,灯光污浊,诱发非典型肺炎的典型昌平夜,地上有些积雪,几日前的旧雪,校园里的雪和街道上的一样,融化着黑色的污浊,踩上去发出咬合般的咔擦声。我们总是看到雪洁白的表象,忘记微观下的狗苟蝇营,沾满汽车尾气,歌舞升平的乌烟瘴气。
直到站在山前,手电的光照亮积雪的原野,光像火一般蔓延,又在目之所及戛然而止。枯涩的草死在白色的荒原,松林的边缘模糊不清。
腰子一如既往地在前开路,我们打开头灯,翻过那道仪式般的铁栏,就像一种宣言,铁栏标志着平行时间线路里另一种生活的分叉,雪反射着光,就像埋葬着冰冻的恒星,腰子站在光斑的中央,像是在倾听黑暗,松林只是回馈给他无限的寂静。
“不要虚,电量充足。”头灯绿色的信号映在白色的雪影。
他打开手电,没有说话,歪着头示意我继续前进,心里估计想的是“老子虚锤子”。
没有灯光的束缚,人反而是夜色里行走自如的动物。
我们踏入山林,冰贪婪地附着山石小径,路很滑,没有冰爪,走起来很费劲。没有雪套,雪倒灌进裤腿和袜子里。
“寒冷是可以克服的,和恐惧一样。”腰子像是喃喃自语,呼出的白气散在光里。
“去你妈的心灵鸡汤。”我笑了,不过如果有热乎的鸡汤喝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轻松地攀上了这座熟悉的山,那块突兀的岩石很幸运地没有结冰。坐在潮湿的岩面,昌平的夜景恰到好处地尽收眼底。
城市无限的生长似乎止步山前,就像饕餮的胃,灯火的辉煌让人恐惧。
“你说,有多少人就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吃的是齿轮转动的流水线排泄的食物,呼吸安之若素的雾霾,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坐在办公室里守着腰围变大,找一个爱或者不爱的人结婚,繁衍后代,和千百年前的人类一样繁衍,然后守着退休金,变得枯朽,最后淹没在时间里。”腰子抽着烟,风夹杂着雪沫。
“这是人的宿命吧,很多人一直到死都没想清楚一生应该怎么去度过,也有人直到临死才想起一生该怎么过。”我说出这句拗口的话,吃着士力架。
“你看到学校了吗?”腰子夹着烟指向前方。
我能看到隐约的灯光,夜色里法大很渺小,每一个光源都很渺小。
“树叶和山石会遮蔽目光。但就像我们逃离学校,现实依旧不会坍缩一样,我们以为自己是在逃离,其实永远走不出当下的束缚。”
腰子咬着过滤嘴,那支烟已经烧到了尽头。
“除非超越时间。”他把烧尽的烟扔在雪地里,残存的火星在洁白的冰冷中渐渐熄灭,就像躺在冰原上的尸体。
“除非我们赶上人类文明的技术奇点,通过人体冷冻技术,越过当下,直抵未来,然后不断跳跃,最后达到时间尽头,虽然时间也许没有尽头。”腰子站起身,城市的辉煌是永恒的背影。
腰子说过,他要以悲壮的方式告别现世,抵达无穷无尽的未来,他要到在南极永冻的冰川里把自己速冻,等待未来人类像挖出猛犸象尸体一样把他发掘,运气够好的话,未来的科技能将他唤醒,腰子教官便能实现火星徒步或者月球露营的梦想了。
我从不觉得他是疯子,我也相信这不是玩笑,如果全球变暖没严重到融化整个南极,腰子说不定真能看见时间尽头。
我们继续出发,绕过林火瞭望员散发橘黄色灯光的温暖小屋,路变得越发难走,乱石堆砌的山脊全是厚厚的冰,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攀过危险的下坡。森林是让人安心的寂静,偶尔有被灯光惊扰的鸟,雪地上偶有不知名小兽的足迹,所有的足迹都会消逝,在下一次新雪里,或者旧雪融化后。
城市无限的生长似乎止步山前,就像饕餮的胃,灯火的辉煌让人恐惧。
黑夜和雪都改变了熟悉的地貌。在某个山嘴处,我们停了下来,这条走过无数次的路居然变得陌生。
我调亮手电想看个究竟,腰子却提议关掉所有光具。
我们关掉头灯,手电。当所有人工装备都停止工作,眼睛逐渐适应黑暗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雪地反射的月光,世界,清晰地一逼。
甚至能看到下一个山头,积雪覆盖的小径在黑色的松林间就像车灯照亮的路标般清晰。
世界进入了单色调,山,松林,岩石是黑色,雪是白色,人是黑色,月亮是白色,夜幕是深蓝色,路变得很好走。
没有灯光的束缚,人反而是夜色里行走自如的动物。
我们抖落满身的松雪回到学校时,还有半小时熄灯。
我打开那瓶可乐,腰子上了下一支烟。
汇入军都楼前的人群,时间又回到了它的轨迹。
鸣谢--感谢可乐能将自己的经历做分享,让其他山友能够从中获益。同时也为他带来的美丽图片点赞。
相关阅读
《再见,永远的阿尼玛卿》——一位在攀登撤营中迷路后,还能镇定辨明方向理智脱险的女生。
(全文完)
雪线之上,你和山野的连接
原创文章,禁止媒体抄袭和无授权转载,保留一切权利
文章某些图片无法联系到作者,如果有侵权,请您与我们联系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ly/83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