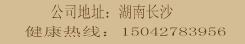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内蒙古和赤峰地区的汉人移民概略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内蒙古和赤峰地区的汉人移民概略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内蒙古和赤峰地区的汉人移民概略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内蒙古和赤峰地区的汉人移民概略
一内蒙古和赤峰地区汉人移民的历史回顾
汉族移民迁入内蒙古和赤峰地区居住,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历史。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地区近期的移民模式,对历史上的移民历程及这些迁移活动给本地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一个综述很有必要。过去的人口迁移模式与社会影响对于我们理解这一地区近代发生的迁移活动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历史上的迁移模式与近代的迁移模式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由于一个地区的地理自然条件、交通旅行条件、居民的传统经济活动都是比较稳定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因此,导致外来移民迁入这一地区主要原因和动力很可能相同或相似,不同时期的移民们在与本地人的交往与整合过程中,也很可能遭遇到相似的境遇。第二个原因是通过信息交流和提供直接的帮助,早期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在原迁出地和目前的迁入地都有可能对近期的人口迁移活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研究人口迁移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所以,我们在解读近期人口迁移和族群交往模式之前,有必要对以往发生的人口迁移历史作一个全面的回顾。
1东周战国时期到明朝的汉人居民与人口迁移
根据历史记载,赤峰一带在周代是北方游牧部落东胡人的活动区域,但汉人自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以来就在今天赤峰地区居住。“公元前3世纪,燕国大将秦开击败东胡后,修了燕长城,设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宁城县黑城,时赤峰市南部燕属之地复为汉人居住,东胡族活动地区已退至西拉木伦河以北”。
元朝时期(1235~1368年),在元朝皇帝直接统治下的内蒙古地区,居住的汉人居民超过200万。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是朱元璋军队与元朝军队作战的主战场,为了躲避战祸,许多汉人迁入毗邻的内蒙古地区。在明朝中叶,有许多汉人农民迁入内蒙古南部(赤峰和哲里木盟)垦殖。根据历史记载,明代在内蒙古中部邻近今日呼和浩特的土默川地区曾有一百多万汉人居民,1790年在今天的赤峰地区生活着11万汉人(参见表4-3)。
2清朝初年和中期的移民政策
据《赤峰市志》介绍,清代汉人移民到赤峰地区有6个渠道:(1)“破产徙入”:入关后,清朝贵族在华北各省大量圈占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户加入流民群进入内蒙古。“流亡来的农民,有的有些资本,到蒙地后从蒙古王公手里购佃土地,开荒耕耘。”(2)“灾荒流入”:华北各省灾害频繁,灾民为谋生流入内蒙古。《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记载:“山东民人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3)“招垦迁入”:自康熙年间开始,赤峰南五旗县和克什克腾旗可自行招垦。(4)“放垦移入”:1840年后,清政府决定废除蒙地禁令,公开放垦,如赤峰在此时期设立以汉人为主的林西县。(5)“公主下嫁带入”:清廷先后有7位公主下嫁今赤峰境内旗札萨克为妻,来时均带大量汉人做工。如顺治五年、康熙三十六年两次公主下嫁,分别带陪房300户和240户,被编为两个佐领。(6)“匠人寻入”:大量汉人工匠被蒙古王公贵族招募入蒙地。
清朝时期关于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和耕种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清朝初期,户籍和迁徙管制较宽松,清廷允许一定数量的“民人”(即汉人)周期性地来到内蒙古和赤峰地区进行季节性耕作。例如,根据史料记载,每年四月到十月,清廷允许800名农民到喀喇沁旗耕作,这些农民既不能携带家眷,也不能跟当地蒙古族妇女通婚。
清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定之后,朝廷对各族之间的交往与人口流动加强了控制,一度严厉禁止移民。1749年,清朝开始严格限制外来农业移民进入内蒙古,主要是担心汉族和蒙古族(中国北方两大族群)一旦联手合作,有可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3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移民政策
在年签订的《瑷珲条约》中,俄国强迫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60万平公里)割让给俄国。通过这个条约,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1858:662)。尝到甜头的俄国此后不断发动边境局部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陆续蚕食中国领土。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53~1860年,沙俄通过武装移民建立堡垒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大片地区,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迫使清朝割让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0年《中俄伊犁条约》和随后几个勘界议定书使俄国进一步侵占了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面对俄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在国内战争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已经非常虚弱的清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中国北部(包括内蒙古地区和满洲)的移民限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在内蒙古、东北移民政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长期限制汉人移民的政策导致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无法有效抵御沙俄武装侵占与殖民,因此“移民实边”成为新的国策。同时多年的国内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捻军、白莲教等)也给中原农业地区造成了损害,其结果是山东、河北、河南和山西等省发生严重饥荒,给清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为了避免大批饥民加入反叛队伍,清政府不得不给他们开放一条求生之路。为了应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清政府开始放松其对中国北部移民的控制。
对内蒙古移民限制的放松要早于对东北移民的限制。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赤峰县有汉民22378人。雍正年间华北大灾,“晋冀鲁灾民大量流入昭(乌达)、卓(索图)两盟,朝廷虽有限制,并规定‘春来秋去’,实际上仍有很多汉民留居下来。至1827年(道光七年)增至112604人”。据《承德府志》所载,热河管辖区内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有汉人557400人,至1872年(同治十一年)则增加到883897人。1878年,清朝开始允许汉族移民到东北三省。
1902年,清朝进一步确定了以“移民实边”政策来代替先前的“借地养民”政策。清廷在各地均任命了负责安排有关内蒙古地区和满洲移民及“垦务”的机构与官员。1910年即清朝覆灭前一年,清朝正式取消了先前颁布的所有禁止在内蒙古地区垦殖的政令,开始鼓励汉人携家眷迁往内蒙古地区,取消了先前禁止蒙汉通婚的政策,允许蒙古族学习汉语。在这一时期,第三条渠道“招垦迁入”和第四条渠道“放垦移入”成为汉人移民的主渠道。
4民国时期的汉人移民
民国政府继承了这些新政策,包括继续在草原地区“放垦”。如1921年,“热河都统汲金纯决定,在阿鲁科尔沁旗放垦荒地108万顷”。1923年,“巴林左翼旗正式放垦”。1925年,“林东设治局在巴林左翼旗贝子庙建立,放垦土地48600顷”。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放垦”对于地方官员有利可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内蒙古地区汉人移民的规模不断增加。
作为这些政策持续实施的结果,1912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超过100万,其中40%在赤峰(表4-3)。第四章的表4-4是1949年及之前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族群的人口数。表中数据根据行政边界的变迁进行了调整,这些数据揭示了蒙古族人口下降而汉族人口增长的整体趋势。从19世纪初到1949年,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人口从110万下降到84万(表4-3),而汉族人口则从50万增加到515万,140年间增长了1078%,年均增长178%。与之相比,同期内全国人口只增长了50%,从3.6亿增加到5.4亿。如果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以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增长,那么其人口只能达到66万,而不是515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1947年前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增长的大部分(60%~70%)应归因于外来移民,而不是自然增长。
5.1800~1949年内蒙古地区人口迁移的三个时期
19世纪初至1949年,汉人在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活动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大约持续100年,从19世纪初到1912年,其特征是移民人口缓慢增加。在这一时期,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44万增加到116万,年均增长98‰(表4-3)。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与饥荒等原因,中国人口整体规模很稳定,从1808年的35亿发展到1912年的356亿。因为清朝对进入这一地区的移民有很多限制,所以,尽管有一定数量的汉人迁入内蒙古,但总体移民规模并不大。如前所述,在早期的汉人移民当中,季节性劳工多于永久性的居民。
在1870年到1912年期间,赤峰地区的汉族人口从11万增加到40万。有关文献强调指出,在1911年之前,位于辽河流域的赤峰和哲里木盟、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套和土默川是当时内蒙古的两个主要汉族定居区域汉人农民向内蒙古的迁移主要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从山西省和陕西省北部到土默川(其中心是归绥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再扩散到黄河河套和伊克昭盟(Ordos),这就是民间俗称的“走西口”;第二条路线从河北(或者从山东经河北)进入赤峰南部的喀喇沁旗,再扩散到赤峰中部和哲里木盟。
第二个时期(1912~1937年)是中华民国建立到“七七事变”之间的25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移民人数快速增长。清廷退位之后,前往内蒙古的移民不再受到任何控制,特别是从1925年开始,移民数量迅速增加,如仅1927~1928年这一年的移民就多达100万人。这是内蒙古地区外来移民的高峰期。而在1925年以前,每年的移民数量都不到50万人,而且当时的移民中“有45%到60%的人返回(原籍)”。
归纳一下,有五个主要因素刺激了这股宏大的移民潮。第一,中原地区军阀连年混战,给各省农业造成破坏,人们想逃离战乱地区,内蒙古是中国北部受战争影响较小的邻近地区。第二,中原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1912~1927年,中国总人口从356亿增加到438亿,当时中原地区城市工业规模很小且受到战争破坏,无力吸收多余的农村剩余劳力。与之相比,内蒙古地广人稀,有丰富的可利用耕地,可容纳中原剩余人口。第三,汉人农民已经在内蒙古建立了许多定居村落,新移民可从已经定居的前期移民那里获得有关的信息和帮助。第四,自1911年之后,内蒙古地区的土地买卖不再受到限制,土地政策的变化鼓励了永久性移民,并且吸引了许多无地汉人农民迁入这一地区。第五,横穿内蒙古的新铁路为移民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铁路的修建以及沿线手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都为汉人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在这25年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116万增加到372万,每年增长率为47.6‰(约为第一个时期增长率的五倍)。
第三个时期(1937~1949年)人口迁入速度明显下降。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372万增加到515万,每年增长率为27.5‰。这一时期汉族人口增长步伐减缓,表明新移民数量比以前有所减少。造成移民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1933~1945年)和国共内战(1945~1949年)。1933~1945年,前热河省(包括今赤峰)被日本军队占领,军事战线的相互封锁限制了农民的流动。这一时期汉族人口的增加,主要是自然增长。在这一时期,赤峰就像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汉族移民聚居区。这两个地方加在一起,大约容纳了内蒙古汉人移民及其后裔人口总数的90%。而这两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汉人移民集中的迁移目的地,是因为具备了吸引移民的重要条件:一是有历史悠久的农业发展和汉人移民史,二是邻近人口密度很高且民众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的汉族省份(赤峰邻近河北省和山东省,呼和浩特地区邻近山西省和陕西省)
二1949年以来内蒙古和赤峰的汉族移民
在实地调查期间,我们能够得到的地方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截止到1984年,同时参考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结果。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一系列复杂曲折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剧烈动荡的政策变迁,这些变动给人们的地域流动和中国各族群间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根据赤峰地区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历程,1949年至1984年这35年间的变迁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时期。由于人口密度的变化直接受到当地移民数量和迁移率的影响,我们在表5-1中通过人口密度这个人口统计指标来考察赤峰地区的人口迁移过程。表5-2是1950~1982年内蒙古区(省)际净迁移人数统计。在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和赤峰地区的人口密度数据时,有一点应当注意,这里的数据表示的只是政府统计的跨越内蒙古与邻近各省之间行政管辖边界的人口迁移情况。
表5-1赤峰和内蒙古的人口密度变迁(1800~1984年)
表5-2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区(省)际净迁移人数(1950~1982年)
1.内蒙古自治区跨越区(省)边界的人口迁移
我们可以把1949年以来内蒙古跨越区(省)边界的人口迁移历程划分为7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0~1952年)是长期战乱之后的社会“经济恢复”期。人们在战火摧毁的工厂、城市和荒芜的农田中努力恢复工农业生产并重建社会秩序,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基层政权和许多新经济制度在逐步建立之中。许多新的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则要到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开工建设。在这三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净迁移人口总数为43.67万人,年平均增长14.56万人,其中迁入人口总数为201万人,迁出人口总数为158万人(参见图5-1),两者平衡后,净迁入人口的数量并不大。在这个时期,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包括汉族、蒙古族和其他族群)每年增加51.7‰,是1937~1949年增加率(22.9‰)的两倍多。
人口的生育数减去人口的死亡数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数。除了自然增长这一因素外,外来汉族移民是内蒙古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把1949年以
前迁入内蒙古的汉族移民因生育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部分扣除掉,并假设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以前时期相同,我们可以判定,1950~1952年迁入内蒙古的移民人数要超过1937~1949年的迁入总数。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华北各地展开的“土地改革”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外迁移民数量也比较多。当时华北地区(河北、山西、辽宁等)农村的“土地改革”(无偿平分耕地)吸引了数以万计在此之前迁到其他地区(包括内蒙古)的农民返回故乡,这些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躲避战乱而离开家乡,在家乡仍有祖坟和亲属。现在家乡的“土改”把地主的土地一次性无偿分给贫苦农户,许多离乡的农民仍被家乡社区接受为本村村民并享有分田资格。这一政策鼓励了部分移民积极返回故乡争取自己的土地份额,并与亲友团聚。虽然我们无法获得有关农民返乡的准确统计数据,但是华北许多农村的土改调查报告可以说明当年一些已迁往内蒙古的汉族农民确实在“土改”期间返回他们在山东、河北、山西、辽宁等省的家乡。第二个时期(1953~1957年)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苏联援助的10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中国的工业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工业生产总值从349亿元增加到704亿元,年增长率为15.1%。全国各城市和边疆地区新建的工业中心为外来移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1957年是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年,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都出现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现象。在中央政府“工业布局”的新规划中,天津、北京等地的许多工厂“成建制”地迁到内蒙古地区的新建工业中心(包头、呼和浩特),被称为“整厂搬迁”。这五年期间,内蒙古迁入人口为418万人,迁出人口308万人,净迁入人口为110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22万人,明显高于第一时期平均每年迁入15万人的速度。仅1956年一年,内蒙古净迁移量就达到35万人。1952~1957年,仅包头钢铁公司一家企业的职工就增加了约10万人,在包头市增长的人口中有84%是外省的移民。自内蒙古迁出的移民则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部分早期移民自愿返乡,二是因为到外省上学或家庭团圆等原因迁出内蒙古。根据内蒙古地方政府的政策,那些未经政府组织安排的自发性移民,无论其迁来后居住在城市还是乡镇,都将被遣送回原籍。因此,迁入人口数量多也意味着政府遣返的人数也很大。
第三个时期(1958~1960年)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高潮时期。受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化方面取得成就的鼓舞,中央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在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和各制造业领域都提出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启动了大量新建项目。与这些经济目标相配合,这一时期全国国有经济部门(工业、运输、贸易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职工人数从2450万增加到5040万,城镇人口从9950万增加到1.307亿。内蒙古的情况也不例外。在这三年中,伴随新的建设项目的展开,迁入内蒙古的移民总数达到499万人,多于前五年的移民总数。除去307万迁出移民,这一时期的净移民量为192万人,平均每年净移民64万人。这一时期的净移民数量差不多是第二时期的三倍。仅1960年这一年,就有230万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成为人口迁移的最高峰。移民的主要因素是中央政府开始在包头建设一个新的钢铁企业以及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新建一批机械制造、水泥、毛纺企业。根据政府统计,1958~1960年,包括区内移民在内,包头市每年净迁入14万人。在这一时期,对自发移民的遣返政策也变得宽松。在大约101万自发迁移到内蒙古的移民当中,有85.4%获得了当地户口并被允许定居,其余的人被遣返原籍。在留居下来的自发移民中,有47.2%的人在迁移前和迁移后都是农民。在这个时期,政府对于外来自发移民的控制相对比较宽松。
第四个时期(1961~1962年)通常称为“经济困难时期”。极度脱离现实的经济发展计划导致各行业生产的严重挫折,粮食大幅减产导致城市食品供应紧张,人民公社制度不得不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经济基本核算单位从人口规模达到几万人的公社调整到只有几十户的生产队。同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并停止所有援助,导致许多工业建设项目被迫终止,其结果是大约2000万职工及其家属离开城镇返回农村。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生产迅速下滑,大量人员被解雇,许多移民被遣返回原迁出的农村。这种经济调整和生产状况也反映在内蒙古的人口迁移活动中。这两年的移民迁入量为104万人,迁出量为173万人,净移民量为-69万人,平均每年约有35万人迁出。内蒙古许多来自邻近省农村的新近被雇佣的工人返回了原籍。城市职工的大幅裁减,在其他汉族省份带来的主要是本省内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迁移,但在内蒙古导致相当数量的省际的移民外迁。尽管如此,这两年从其他省迁到内蒙古的自发性移民据统计仍有约9万人,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河北和山东遭受饥荒的农民,到内蒙古寻找生计。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有关政策,这些人中有97.3%的人在迁来的同一年即被遣送回原籍。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移民事件,这就是从1960年到1963年。在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乌兰夫的组织下,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多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他们被牧区的蒙古族牧民家庭收养。当时这些沿海省份粮食缺乏,各孤儿院的粮食供应非常困难,经周恩来总理与乌兰夫商议,内蒙古牧区接受了这些汉族孤儿。
第五个时期(1963~1965年)通常称为“经济恢复和调整时期”。这一时期标志着经济计划平稳发展的开始。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及时调整修正了经济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由政府按照每人定量保证粮食供应,农民的粮食自行生产。为了确保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在这一时期政府严格控制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这种控制对省际移民也有某种负面影响,因为迁往内蒙古这些边疆地区的移民中,有相当部分属于从汉族省份的农村前往边疆城市的“农村—城镇”迁移。1949~1983年,包括跨省区移民在内,内蒙古的“农村—城镇”类型的移民约占省区际迁入移民的36.8%。这期间,迁入的移民数量(126万)与迁出的移民数量(121万)非常接近。内蒙古地区净迁入移民数量仅为6万人或每年约2万人。
内蒙古作为一个边疆地区,一些新规划的建设项目在此期间继续得以实施。例如,11家工厂连同工人及其家属约2万人从天津迁到了呼和浩特、包头和集宁,占这一时期内蒙古净迁移量的1/3。与之相比,迁往农村地区的移民数量非常小。另外,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在自发迁入内蒙古的6.57万人(绝大部分不是农民)当中,有99.4%被遣回原。
第六个时期(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复杂的政治运动相联系,社会动荡不安,人口迁入迁出时常发生。例如,在1968~1973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全国有约800万名城市学生下乡,1974~1976年全国又有497万名城市学生下乡。根据政府统计,在“文革”期间约有其他省市的10万学生迁到了内蒙古,“文革”结束后,这些知识青年有72.8%的人返回城市。这11年间,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迁入总数为545万人,迁出总数为522万人,净迁入量仅为23万人。换句话说,每年有大约50万的移民迁入,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移民迁出,平均每年的净迁入移民仅2万人。所以,这一时期的迁入净增长等于1963~1965年的净增长,同时有大量的移民(外省下乡知识青年)回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社、大队这些基层政权一度瘫痪,失去了对本应全部遣回原籍的自发性农民移民的控制。根据政府统计,1966~1969年,有25万自发性外省农民迁移到内蒙古农村定居。
第七个时期(1976~1982年)被称为“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基层政府失控而迁入内蒙古的一些自发移民在“清查”过程中被遣返回其原籍,一些在20世纪50年代因参加“支援边疆建设”项目迁到内蒙古的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因退休或其他原因迁出内蒙古回到原籍省市,“文革”期间从北京等城市来到内蒙古“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大部分返回原籍,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出现了人口净迁出的现象。这一时期内蒙古迁入总人口为320万,迁出总人口为340万,净迁出人口20万人。这时期的特征是进出的移民规模都比较稳定。每年迁出人口和迁入人口各约50万人,迁出人口数量稍高于迁入人口数量(图5-1)。
2.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内人口迁移
根据人口户籍登记的统计材料,在1950~1984年这40多年里,内蒙古自治区内的移民总量估计达到70万人次;但是如果“往返式迁移”和“迁入—返回式迁移”被排除在外,那么“单向”移民的数量仅为10万人左右。其中,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吸引了其他省和内蒙古其他地区的许多移民。1952年,包头市总人口为12万人,但是到了1960年,人口就增加到94万人。以包头市的发展为例,内蒙古城市化速度高于全国水平。在1968~1976年下乡“插队”的中学生里也包括内蒙古其他城市的知识青年,如锡林浩特的中学毕业生下乡“插队”到东乌珠穆沁旗的下属公社,其中许多人在“文革”后也返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
自治区内的“农村—农村”类型的移民大多属于从临近河北、山西以及辽宁等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省的南部省界地区(如赤峰南部的宁城县和喀喇沁旗)迁往人口密度低的牧业地区(如赤峰北部的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参见图4-2),但是很难找到这一类型移民的具体统计数字。整体而言,农业移民的大方向是由人口密度高、自然资源(土地、牧场和森林)有限的地区向人口密度低、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迁移。几个世纪以来,正是这种对土地资源的追求引导汉族农民从河北等地向临近的内蒙古南部迁移,把那里的牧场转变为半农半牧区。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这些半农半牧区逐渐变为纯农区。而随着人均耕地数量的减少,部分农民继续向北部牧区迁移。汉族农民向北方的持续迁移,最终遇到大自然设置的“农业发展界限”。北部地区较短的“无霜期”、不适合农耕的沙地土壤、稀缺的降雨量等限制因素不仅使得农业耕作无利可图,而且无法生存,严重的沙化强迫农民放弃在当地的农业耕作而迁回南部。在赤峰所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形,在后面对有关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将做更加详细的讨论。
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口变迁模式,国内人口学界在1980年提出了“三个600万”的提法:第一个600万,指的是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为600万(实际数字是608.1万);第二个600万,指的是这600万人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翻了一番,增出新的600万(实际是713.42万);第三个600万,指的是在这30年内因为人口迁入和移民的生育,内蒙古新增加的600万人口(实际数字是530.28万)。从这个粗略的归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口迁移对内蒙古人口变迁的显著影响。
3.内蒙古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在1949~1982年,无论是从外省市迁往内蒙古还是内蒙古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都具有如下特征。
(1)迁入内蒙古的区外移民的主要迁移目的地是城市地区,特别是两个新的工业中心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这两个新兴的城市地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水平,迁入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区外移民都是政府组织和安排的,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自发移民受到城市建设计划的影响。在1953~1960年,外来移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内蒙古的农村地区。但是在1960~1979年,来自附近省份的农业移民有所增加,内蒙古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将其遣返原籍。根据官方的统计,在1961~1965年,这一政策似乎很有效,但是在1966~1976年即“文革”期间,这一政策无法有效地执行。1963年以后的移民主要是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村地区向内蒙古农村地区的迁移。由于政府统计的数据主要涉及的是有关省区际移民的,因而我们无法考察自治区内部的移民数量和迁移模式。
(2)“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返回式迁移”。城镇知识青年由政府安排集体下乡在公社当社员,在几年后又逐渐返回城镇。在这一特殊类型的迁移中,有些属于省区际的迁移,但大部分还是自治区内部的迁移。有些政府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可以被包括在这一类型中。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安排迁到内蒙古工作,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他们到了退休或接近退休的年龄时又返回其原来所在的城市。
(3)内蒙古净移民增长的曲线轨迹是“稳定(1950~1955年)——增长(1956~1958年)——快速增长(1959~1960年)——下降和负增长(1961~1965年)——稳定(接近于零)(1966~1982年)”(图5-1)。人口迁移的这种波动与外省农民迁入内蒙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省份出现重大自然灾害。
(4)移民的结构性特征如下:根据198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样本量为20万人的抽样调查结果,如果出生在其他省区的人口即被定义为“移民”,那么移民人口在内蒙古调查总样本中占13.2%,其中城市居民当中有28.8%为移民,在农村则仅为8.0%;在汉族总人口中,移民占15%,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移民仅占4.3%;移民的来源省份依次为辽宁(22.4%)、河北(19.9%)、山西(11.5%)、山东(11.5%)、吉林(10.6%)、黑龙江(6.9%)、陕西(4.8%)、甘肃(3.8%)、河南(2.4%)、江苏(2.4%)、浙江(1.2%)、四川(1.1%)和宁夏(0.6%)。在内蒙古各盟市中,赤峰市(昭乌达盟)调查样本中35岁以上人口中的移民比例最低(3.9%),其余盟市人口中移民所占比例较高的分别为乌海市(80.1%)、哲里木盟(79.6%)、阿拉善盟(73.6%)、包头市(55.5%)和呼和浩特市(28.0%)。
三 汉人移民对内蒙古和赤峰迁入社区的影响
内蒙古(包括赤峰地区)长期的移民史和大量移民的迁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当地的地理景观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有一首古诗是这样描写蒙古草原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在赤峰南部,开垦的耕地和密密麻麻的村庄已经取代了往日那种辽阔的草原,汉族农民成为这一地区居民的大多数。
图5-2大致列出了汉族移民对赤峰本地社会的主要影响。移民在多个方面改变了这里的传统状况。
1.移民增加后带来的三个直接影响
(1)人口密度显著增加(参见表5-1)。自1912年以来,像内蒙古其他地区一样,赤峰的人口密度迅速增加。从历史上各朝代乃至民国时期,赤峰一直是南部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的主要定居点,其结果导致1983年赤峰的人口密度是内蒙古全区人口密度的近3倍。
1979年赤峰各县旗的人口密度情况如图5-3所示。南部宁城县、喀喇沁旗和郊区(即前赤峰县)的人口密度高于其他旗县。在20世纪初期的“放垦时期”,林西县和巴林左旗是本地区两个重要的农业移民定居点,所以其人口密度在赤峰北部诸旗县中相对较高。赤峰地区总体的人口密度是南部最高,人口密度由南往北逐渐降低。
(2)大规模的农民迁移到赤峰各地后,把自己传统的农业耕作生产方式带入这一传统的牧业地区,将当地的草场开垦为耕地,他们的迁入改变了赤峰地区的整体经济结构。如前所述,大部分移民在迁移之前就是农民,他们迁移的主要动机就是寻找新的可供开垦的土地。在早期汉人移民进入内蒙古时,他们从本地的蒙古王公贵族那里私自租种土地。19世纪后期清朝逐渐改变其移民政策后,朝廷允许蒙古王公贵族公开招募汉族农民,甚至为“放垦”事务设立了专门机构。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赤峰下属的许多地方转变为农业区,许多当地的蒙古族居民也从牧人转变为农民。在1965年的内蒙古地区,牧民(包括汉族和其他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约有50万人,蒙古族农民超过70万人(如果包括以前曾是蒙古族聚居区现属其他省份的蒙古族农民,其数量将超过100万人)。日本人为了实现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的领土野心,自19世纪后期即开始派遣大批特务以各种公开身份收集中国东北、内蒙古及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人口资料,绘制地理、交通、矿产、人口地图。日本人在1916年分别绘制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农业-畜牧业分布和蒙汉人口分布地图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初内蒙古东部的基本情况(图5-4,图5-5)。根据图5-4和赤峰市政府提供的1982年以户籍等级为依据的农牧业人口分布数据,我们把这两个历史年代赤峰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业地区的分
布情况在图5-5中展示出来。在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60多年里,赤峰地区农业耕种面积得到显著扩展。
大约三百年前,赤峰地区曾经是一个辽阔的草原牧场,但是到了1916年,赤峰南部的大片土地已经转变为农田,仍旧保持传统畜牧业的土地仅剩下北方和东北部分。如前所述,农产品的价值是牧业产品的两倍(表4-2)。到了1982年,我们发现农业区反而向南方收缩,一度已经成为半农半牧区的阿鲁科尔沁旗南部和翁牛特旗东北部又转变为牧区。林西县部分地区和克什克腾旗东部的农区也转变为半农半牧区,克什克腾旗北部的纯牧区也有所扩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地理气候和土壤植被因素对农业的客观限制是否起到关键作用,迫使经营困难的农田又重新转回为牧场,这些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3)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显著改变了内蒙古地区的族群人口结构。如表4-3所示,1912年赤峰地区汉族人口的规模大约为蒙古族人口的1.4倍,而到了1983年,汉族人口成为蒙古族人口的7.4倍多。汉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移民。图5-6是日本人绘制的1916年内蒙古东部蒙古族、汉族人口分布图。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期,内蒙古与南部省份接壤地带已经变成汉人居住区,昭乌达盟(今日赤峰)的中部已成为蒙汉两族混居区,而且有些纯农业区已经出现在北部的半农半牧区当中了。日本人在1916年绘制的族群人口分布地图也许并不精确。例如在图5-6中,赤峰的中西部地区(克什克腾旗南部)已标志为汉族地区,但根据《赤峰市志》和《克什克腾旗
志》等档案材料来看,当时这一地区更像蒙汉混居地区。这幅地图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年代最早的内蒙古族群人口分布地理图,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这幅日本人绘制的地图和赤峰市提供的资料,我们绘制了1916年和1982年赤峰市蒙古族、汉族人口分布图(图5-7),以便对这几十年的民族人口居住格局的变迁进行比较。
我们根据1982年赤峰市人口普查数据绘制1982年民族人口分布图时,把蒙古族居民少于总人口10%的地区看作“汉族居住区”,把汉族居民少于总人口10%的地区视为“蒙古族居住区”,处在两者之间的定义为“蒙汉混居区”。这样的定义可能使“蒙汉混居区”内包含了各族人口比例差异很大的不同区域,如汉族占80%的地区和蒙古族占80%的地区都被定义为“混居区”。我们把“混居区”的范围定得比较宽,这是因为从民族间的交往而言,我们认为超过总人口10%的群体已经可以有相当多的机会与另一个群体进行交往了。
从图5-7中可以看出,自1916年以来“汉族居住区”的面积显著扩展,现在已经占据了整个赤峰的南部地区。1982年在赤峰的中部,从东到西是一
片狭长的族群混居地区,包括了5个旗县政府所在的县城。县城通常是政府机构(党政机关、法院、公安等)、公共服务设施(医院、学校、邮局、银行、电力、公共汽车站等)、商贸中心(旅馆、商店、加工厂、集贸市场等)的所在地,在这些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多数是汉族。另外在这些县城附近也有一些自发形成的汉族农业区,向县城居民提供蔬菜、禽蛋、肉食、副食加工等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些汉族农业区又逐渐在各县城之间沿着公路线延伸和连接起来,并逐步向两旁扩展。与之相比较,以蒙古族居民占绝大多数的“蒙古族居住区”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主要集中在交通不发达的草原地区。
在赤峰南部和中部的汉族居住地区当中,有4个主要城镇(赤峰市及喀喇沁旗、敖汉旗、翁牛特旗这3个旗县的行政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在1982年属于族群混居区。而1916年的族群分布图并没有反映出这种情况,该图显示当时的赤峰县和乌丹县都属于“纯汉人区”。那么,在此期间这两个城镇的蒙古族人口是如何增加的呢?这一变化可能有几个原因。早在1778年,清朝就在原乌兰哈达直隶厅的基础上设立赤峰县。乌丹是赤峰地区较早的汉人定居地区之一,1937年在日伪统治时期设置乌丹县,是赤峰中部的汉人聚居地区。所以,日本人在1916年把这两个城镇及周边地区归入“纯汉人区”是有道理的。在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中央政府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强调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自治区内鼓励蒙古族成员积极参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以及各种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在这种政策引导下,作为昭乌达盟首府的赤峰市吸收了大量蒙古族干部和各类从业人员,使赤峰市(包括郊区即原赤峰县、元宝山区、红山区)的蒙古族人口所占比例达到13%,因而成为“蒙汉混居区”。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把乌丹县制撤销并入翁牛特旗,也体现了这个蒙古族自治区的区域自治政策,旗政府各级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蒙古族,这一行政区划调整也使翁牛特旗政府所在地的乌丹镇成为“蒙汉混居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赤峰西部的克什克腾旗,其首府经棚镇在1916年族群分布图上显示为汉人居住区。1914年民国政府在此地正式设立了经棚县,“辖汉民4.8万人”。1933年日军侵占此地后,“撤销经棚县,并入克什克腾旗,建伪旗公署”,1945年再次设立经棚县。1948年,“经棚县并入克什克腾旗”。与赤峰和乌丹的情况一样,新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旗县政府和下属机构积极吸收蒙古族干部、知识分子和从业人员,也使这些城镇成为“蒙汉混居区”。这一族群人口分布模式的重新调整也体现在1982年的族群人口分布图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成立后,加强蒙古族自治地位的政策也体现在区内各地一系列的行政建制调整中,如乌丹县并入翁牛特旗,经棚县并入克什克腾旗。可以举出的另外两个例子是新惠县与敖汉旗的合并和建西县与喀喇沁旗的合并,在这些合并中都保留了旗的名字而取消了县名,体现出蒙古族在自治区作为自治族群的主体地位。蒙古族人口在各城市地区的集中不仅反映在赤峰地区,呼和浩特等其他主要城市在1949年以后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使许多蒙古族(干部、知识分子、教师、工人)集中在自治区的各行政中心城市及其附近地区。
2.移民大量增加带来了三个间接影响
大规模移民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上述三个主要方面(人口密度、社会经济结构、人口族群结构)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影响又进一步在以下三个领域造成了深刻的间接影响或产生了三个矛盾(参见图5-2)。
(1)人口密度的迅速提高(表5-1)给当地的自然资源造成很大压力。内蒙古地区按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耕地面积从20世纪50年代的12.3亩下降到1981年的5.6亩。1981年,赤峰地区的人均土地面积为4.1亩,低于内蒙古全区的平均水平。赤峰地区的许多土地(例如翁牛特旗东部的流动沙丘和盐碱地)并不适合于农业耕作,开垦以后收成很少。1982年在赤峰市下辖的10个旗县中,林西县每亩耕地的农作物产量仅为84斤(或629公斤/公顷),有5个县旗的平均亩产在100~200斤,两个旗县的单位产量是200~300斤,两个旗县的单位产量是300~315斤。1982年赤峰全市的平均水平是212斤/亩(或588公斤/公顷)。这大大低于该年全国平均416斤/亩(或3117公斤/公顷)的水平。我们在赤峰各旗县进行实地调查的村落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抱怨土地缺乏,并且特别强调当地的土地质量太差。
大量移民的迁入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加剧了土地供给的压力。由于内蒙古大部分土地的肥力很差,这里的农业生产仍然属于粗放型的,很大比例的农田属于山坡地,没有南方农田的传统田埂和灌溉沟渠,被称为“漫撒籽”,收成多少完全靠自然降雨,作物产量的提高依靠的是不断扩大耕地种植面积而不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农民们为了扩大耕地,不断把周边的天然草场开垦为农田,同时放弃那些耕种几年后产量逐年下降的耕地。但是,大自然也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土壤质量、降雨量以及无霜期等因素,有些土地只适合作为放牧的草场,而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大自然的生态体系已经规定了利用各类土地的最适宜的方式,人类一旦跨越了大自然划定的“生态边界”,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由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努力改变大自然设定的这些生态边界,比如在某些地区建立灌溉系统(修建水渠、滴灌系统)以改变一些土地的缺水状况,但是这些努力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各种限制。
内蒙古的土壤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a)栗褐色土壤;(b)沙地和半沙地(约占内蒙古面积的20%);(c)肥沃的黑土(赤峰和哲里木盟南部以及土默川地区)。热衷于开垦荒地的农民逐渐跨越了黑土和栗褐色土壤之间的边界,进入栗褐色土壤地带。他们每年播种但没有对土地施加足够的有机肥,农作物的生长使土地日益贫瘠并被灌溉用水的盐碱所侵蚀。当农民们把属于半沙地性质的天然草场开垦为农田以后,耕作两三年后,土地就失去过去积蓄的全部肥力,之后种下的作物几乎没有收成,于是农民不得不放弃这些土地转而开垦新地。但是,这几年的耕作却破坏了地表下层原有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系。全年大多数时间里,这些被开垦的土地上都没有季节性的农作物生长,即使在4~10月的农作物生长期,这些农作物的根系很浅也无法覆盖并固定地表土壤。每年春天,蒙古高原强劲的大风便吹走了地表的土壤,使那些以前与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交织在一起的黄沙翻露到地表上来,造成地表的严重沙化,大风和干旱又使这些沙土变成了移动沙丘。自19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已经变得日益严重。休(E.R.Hue)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50年代内蒙古一个地区的生态景观。
直到17世纪中叶,……整个地区的景观仍然呈现出一种粗犷的伟大;茂密的森林覆盖了山脉,金色牧场中的蒙古帐篷映白了山谷。(但是当汉族农民)获得开垦荒地的许可后,……原野的面貌就被整个地改变了。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殆尽,森林在山坡上消失,大火吞噬了草原,新来的垦荒者们开始忙于耗尽土地肥力的耕作……干旱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尘土遮天蔽日,空气变得浑浊。(引自Myers,1956:507)
这是当年一个外国观察者对不当的垦殖活动如何破坏内蒙古草原的生动描述。这是大自然对人类忽视生态规律的惩罚。新中国成立后,在赤峰地区人为的生态破坏活动仍然延续。1985年我们访问赤峰时,得知曾经覆盖赤峰市南部山冈的松树林,在“大跃进”时期的“全民炼钢”运动中被全部砍光,现在不得不重新种植。自1949年以来,赤峰各地开垦新耕地的现象仍在继续进行。直至今日,一些急功近利的农民仍然忽视大自然的规律,整个内蒙古地区包括赤峰的生态破坏依然十分严重。在过去十年中,根据有关科学家和农业专家的建议,政府已经开始限制开垦新耕地,鼓励种树种草,特别是在半沙化地区鼓励种植可以控制移动沙丘、防沙固沙的各类灌木。可以说在过去十年里,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和对保护草原提供的项目资金已经大大改善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
然而,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密度的提高持续给人均自然资源(耕地)带来沉重的压力,人们为了生计仍然会偷偷开垦新的土地,导致政府统计的耕地面积与农民种植的实际面积之间有不小的差距。这样的私自开垦必然带来严重的生态后果。在赤峰地区,这是移民和人口密度增加后出现的第一个矛盾:人的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即生态矛盾。
(2)由于汉族农民大量迁入以及他们对新耕地的开垦所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蒙古族牧民可供放牧草场面积的显著减少。在当地社区转变为半农半牧区以后,本地的蒙古族也加入了开垦的行列。这一问题以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类型彼此竞争土地资源的矛盾体现出来。在历史上,内蒙古耕种农业的发展严重损害了传统畜牧业的发展,这一矛盾在今天的半农半牧区尤为明显。
近代在内蒙古地区发生的土地使用权之争曾导致严重的暴力事件。清朝后期的“垦务局”经常遇到当地蒙古牧民“武装保护牧场”的反抗,在某些地区清朝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镇压。例如1800年和1821年,敖汉旗蒙古牧民曾两次驱逐汉族农民,清政府不得不居中调停。实际上,这些都是蒙古族贫穷牧民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将部落公共草场出租给汉族地主和汉族农民的运动。这些冲突通常导致汉族农民从草原地区被驱逐出去。在草场拥有者(蒙古王公贵族)、租用者(汉族地主)和开垦者(汉族农户)之间的冲突中,最大的获利者是蒙古王公贵族(他们获得大量租金,几乎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和汉族地主(他们以较低租金从蒙古贵族手中租来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然后将租来的土地分成小块,以较高租金出租给汉族农民从中获利)。由于内蒙古“放垦”土地的租金低于其他省份,租种这些“放垦”土地的汉族农民也得到了部分利益。利益受损最大的是贫穷的蒙古族牧民,他们无权将土地出租给汉族,而“放垦”之后,他们可以放牧的草场面积却越来越小。
在今天的内蒙古,农业和畜牧业在土地使用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政府鼓励农民将贫瘠而不适宜农耕的土地再转变为牧场,以恢复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在一些生态严重恶化的地区组织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生态项目,并提供了专门的资金来帮助因为这种转换遭受损失的农户。另外,由于畜牧产品短缺以及国家对少数族群牧民提供多种优惠政策①,从事畜牧业的收入较高而税收较低。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也迫切希望当地政府能将其户籍身份从“农业户口”改为“牧业户口”,从而少交税并从政府那里多得到一些财政补助和项目资助。但是,这种户籍身份更改并不必然意味着那些被认定为“牧业地区”的农民会将现有的大片耕地转变成牧场,也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会停止对现有草场的开垦。而真正的“退耕还草”才是政府同意变更户籍身份的主要原因。
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平衡,在一个具体地区的生态环境中两者各自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在生态已经遭到破坏的地区如何逐步恢复生态平衡,如何控制土地的进一步退化,如何调整农作物生产和放牧对土地的合理使用,以使这种调整真正为本地居民所接受,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由于移民发展耕作农业而产生的第二个大问题,即农业与畜牧业在土地使用方面的矛盾。
结束语
伴随内蒙古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蒙古族在教育、医疗、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全面改善,新中国的族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蒙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个族群间不存在问题。在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地区,牧民(通常是蒙古族)和农民(通常是汉族)在土地使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在牧业地区,一些汉族农民抱怨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学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同时,一些蒙古族村民也抱怨他们公社和生产队的耕地在不断扩张。由于可供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少,即使他们不愿意,这些传统的牧民们也不得不放弃牧业而变成农民,但他们对耕作农业并不熟,因而收成不好,比起他们的汉族邻居他们更加穷困。而我们在村中访谈的汉族农民则说,他们的蒙古族邻居之所以更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耕作。赤峰市的一些出身蒙古族的领导人也向我们谈到蒙汉族群之间的收入差别。在这个地区,人们的一般印象是蒙古族受的教育较少,因而收入也较少。但是一般性的观察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实际的社会情况。对这一地区农村蒙汉村民之间结构性差异的评估必须以统计资料和调查分析为基础,而不能仅仅凭靠可能存在偏差的一般印象。这就是由移民产生的第三个问题:由汉族移民、土地资源紧张、农牧矛盾而引发的本地蒙古族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放垦”,这种矛盾在近代曾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自1949年以来这些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在今天,由于资源竞争、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蒙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由于移民的大部分是汉族,因而蒙汉之间的交往整合与移民-本地人的整合密切相关。由于多重因素在互动中彼此影响,这也使本项研究所中科白癜风公益惠民活动招聘(竞价)主管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ly/19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