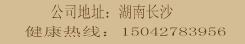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别看姥姥不认字,却崇尚文化丨雷音夜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别看姥姥不认字,却崇尚文化丨雷音夜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别看姥姥不认字,却崇尚文化丨雷音夜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别看姥姥不认字,却崇尚文化丨雷音夜
日坠山涧,寺钟响起,
洗尽了铅华,感受夜凉如水。
在青灯烛影之中,
享受一次心灵抚摸,倾听一段动人的故事,
这里的夜,
不属于诗人,
而属于那些孤寂的灵魂。
■文|倪萍
其实姥姥从做第一顿饭开始就是用心做,姥姥说过了,啥事用心做,你就成神了。
姥姥包的包子你吃了这个还想拿那个,吃多少你都觉得不饱。
发面的包子咬一大口才能吃到馅,可是皮比馅还好吃,为什么呢?
因为皮的一半是浸了油的,包子里的肉块一定是好的,五花肉有肥有瘦,还有弹力。
不论什么菜都是切大块的,姥姥说这样有嚼头。
如果是烫面包子,姥姥包的皮,那个薄啊,都快成透明包子了。
从外面就能清楚地看到姥姥包的是发面包子,要到半凉半热的时候吃着才有味儿,烫面的姥姥说一定要趁热吃。
蒸包子的时候姥姥也特别讲究,包子底下要垫上玉米叶。
一是不沾笼,二是有玉米叶的香味。
蒸熟了不要马上拿出来,要晾一会儿,省得他们往一块粘。
皮薄的包子不好看,包子上面还得盖上一个笼屉布,风吹了,包子皮皱了,也不好看,皮硬不好吃,姥姥包的包子个儿特别大。
她说包子小了,那你就不如吃饺子了。
她包的饺子也比一般人家的大,姥姥说小饺子吃不出味道。
姥姥说饺子煮在锅里,要长得像一群小飞猪一样才好吃,煮的时候别煮多了,要几个几个的煮。
让吃的人从第一个饺子吃到最后一个都是刚煮出来的,姥姥包的虾仁饺子那个好吃啊。
首先,虾必须是渤海湾海里最小的那种虾,这种虾胶东半岛特别多,包进饺子里的虾基本上一刀只切两三段,不能太碎。
馅里的韭菜必须是6月份以前的,姥姥说了,6月韭,臭死狗。
如果再切点花肉提提味那就更好。
包的时候都是两手一捏,大肚子就出来了。
吃的时候也别一口吞下去,得吃两口,这样才能吃出饺子味儿。
每年鲜虾上市的时候,妈妈都是几十斤的往家买。
姥姥就坐在厨房里剥虾皮,剥好的虾仁用保鲜袋封好,然后放进冰箱里。
整个春天我们就隔三差五的吃顿虾仁饺子,儿子早上上学起来,姥姥都给他做虾仁饺子。
姥姥认定虾吃多了,孩子能长个儿。
唉呦姥姥,我儿子可不敢再长了,长那么高又打不了篮球。
你说将来安灯泡不用梯子,所以人家问七岁的儿子长大了干什么,他说当梯子,其实谁都不明白这出处在哪儿。
我姥姥烙的饼真的比印度抛饼好吃多了,放在锅里是一张饼,谁都不粘着谁,想撕下了一块,你还挺费劲的。
姥姥把包子、饺子、烙饼的秘方都传给我了,弄得我如今很辛苦,上我家来的朋友都是点着名要姥姥包的包子、饺子。
如今姥姥不在了,自然是姥姥的外甥——我来包。
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包的也很好吃。
反正吃的人都会说剩下的我带走吧,还有人建议我开个包子铺。
你说瞧我这点出息,我不能从春节晚会上下来,再开个包子铺吧。
主要是姥姥用心包的,这种包子成本太高了,我包不起。
姥姥活着的时候我批评她,做个饭干嘛那么费劲,多浪费时间。
你猜姥姥怎么说?
“我这辈子就这么点事儿,再不费心,我那么闲着干啥?心闲着闲着就麻了,麻了就跳得慢了,慢了就上床躺着,躺着就是心脏有病了。”
“就是无病呻吟吧?”
姥姥过日子用心体现在方方面面。
一捆柴禾四用,烧火做饭的时候就把炕上的被子铺开了,先捂着(锅灶连着里屋的炕)。
锅上熥着饭,锅底熬着米汤。
大火开了锅,风箱就不拉了,余火里埋上地瓜、土豆,冒着热气的锅盖上还搭着冰冻了一天的衣服。
姥姥从来不浪费资源,也不浪费时间,和邻居闲扯着,手里择着菜,熬粥的地瓜干都用手掐得碎碎的,说是省火。
节省了一辈子的姥姥偏偏养了我这个最浪费的外甥,什么东西都往垃圾桶里扔。
解不开的线圈一剪子就咔嚓了,洗不掉污渍的衣服,扔!再好的菜吃不完,扔!
我跟姥姥说,我是不是得改改这毛病?要不按你说的我这下辈子得要饭呢。
唉,姥姥倒说不用改:“对你这样的人来说,心思、时间都花在省碗菜、蹭蹭油锅上那就不上算了,有这工夫你去随便干点别的事,那就能挣一篮子菜,一锅油。人和人的本事不一样,老天给他安排的事儿也不一样,俺这些人没本事,才穷过穷打算。”
姥姥辩证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与时俱进哪。
我想起上小学那会儿,姥姥跟我住在青岛。
那时候买粮都得用粮本,正长身体的我和哥哥总觉得吃啥都吃不饱,可是姥姥吃啥都是吃那么一点点。
哥哥经常拿着放大镜照着姥姥的肚子:“啊,姥姥没有胃。”
姥姥说:“你再照照你自己,俩胃。”
全家人都大笑。
小时候的哥哥无视任何人,好吃的都是吃双份。
当年西哈努克亲王访问青岛,我们代表青岛的小朋友给他们献花的时候,得了一份夜餐——大众饼干。
我没舍得吃,双手捧着从青岛火车站走回家,想给姥姥和妈妈尝尝大众饼干。
回到家还没看清饼干长得什么样,就进哥哥的肚子了,气得我直哭。
姥姥去安慰我:“行啊,你得了个面儿,眼吃饱了;你哥眼饿着,肚子饱了,这不挺好的。”
姥姥说对了,即使40多年过去了,再从电视上见到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我都会想起在我七岁那年见过他。
这不就是眼饱的好处吗?
那个时候最怕吃饭的时候家里来人。
有一回我们家的饭刚摆上桌,就人敲门。
姥姥噌的一下站起来,随手就拉下了灯绳,“家里没有人”。
哥哥和我都笑了:“家里没人你还说话呀,姥姥?”
“大娘,我是倪会计单位的,来送大葱的,给你放门口了。”
姥姥啊,那时候就怕外人进门吃饭。
人家多吃一口,她的外甥就得少吃一口。
“家里没人”这句话,那时候说起来就想笑,现在想起来挺难受的。
你要知道在水门口,姥姥家的门从来都是关不上的,谁进门只要赶上个饭点儿,姥姥随手就会搬个小板凳来,“过个门槛吃一碗”,一句顺口溜让人吃得心安理得。
那年月,即使刚吃了饭的人坐下来轻松地喝上两碗面,肚子都是空的,没有油水。
要不,现在只要有人说共产党不好,姥姥就反驳:“你别不知足,你去试试,让这么些人吃饱喝足,谁也不行,也就共产党有个好章程(办法)。”
姥姥对党有感情,对毛主席有感情,对这个国家有感情。
他的儿女、孙子、外甥几乎都是党员,她觉得这一点她很光荣,她很有面子。
年香港回归祖国,我带姥姥去人民大会堂看节目。
我做主持人二十几年了,这真的是我第一回利用工作之便把家里的人安排到现场。
姥姥前排坐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姥姥觉得她一个普通老百姓离党那么近,她很不安。
我告诉姥姥我说你应该坐在这儿,你是革命烈属,你是英雄的母亲。
那天晚上姥姥脸上放着从未有过的光彩,她内心一定体验着光荣,体味着自豪。
无论谁,无论有文化没文化,光荣与梦想都埋在她心底的深处,一旦有机会它就会闪烁。
那晚姥姥真是高兴了。
看看舞台上唱大戏的人,再抬头看看那么高的房顶,她一定是想起了60年前她家盖的那五间大瓦房,二十几个人才把房梁上上。
这么个大会堂,这么大的房子,你说上梁的时候得多少人呢?得蒸多少馒头啊?人哪,真是能气呀。
演出结束了,我和姥姥就坐在大会堂的台阶上。
我说:“姥姥,你看今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的,多漂亮,好吧?”
“嗯,好是好,就是有那么一点不好。”
“哪点儿不好?”
姥姥指着毛主席纪念堂:“就差那么点电啊?该都点上灯……”
我一看,可不是嘛。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处都挂着彩灯、串灯唯有毛主席纪念堂那块是暗的。
“没有毛主席,中国不会那么早解放,该都点上灯,就差那么点电……”姥姥反复说着这句话。
你看我姥姥,用词之准确。
“该”而不是“应该”,“就差那么点电”,姥姥的意思“顺便儿”就挂上了。
这里面包含着她对毛主席的评价。
姥姥啊姥姥,从来没和这个时代脱节过。
不认字,不上班,家里的小事、国家的大事她其实都明白,不白活呀姥姥。
小平同志去世那天,姥姥还在家里专门找出王文澜曾经给小平同志拍的一张照片摆在桌子,正中间点上三炷香,鞠了三个躬。
“姥姥,你不上学真是可惜了。”
“不可惜,我要去念了书、上了班儿,你还能有你们?”
姥姥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抚慰自己,只有姥姥知道。
姥姥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姥姥和季羡林是同学。
前些年,季老的一些散文、杂文刚上市那会儿,我们就买了很多,没事就在家念给姥姥听。
虽说是大学问家,可书里的国事、家事都写得那么入情入理,不矫情也不做作,大白话里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书姥姥爱听,有些段落我反复给姥姥念。
日子久了,姥姥会经常打听这个老头的一些事儿,我也一遍一遍的把我知道的、听说的、书上看的跟她详细的说。
慢慢地,爱翻书的姥姥手里又多了几本季老的书。
有一天我回家,看见姥姥手捧一本季老的杂文,戴着老花镜坐在那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全都笑了。
生人要是第一次看见这场面,一定以为姥姥是一位做学问的教授呢。
你别看姥姥不认字,却崇尚文化。
在姥姥的秤上,字的分量最重,书最值钱,多贵的书姥姥都说值,都说便宜。
“二十几块钱买啥?买个吃的一会儿就吃完了,买本书能起吃一辈子。好的书下辈儿又接着吃,上算。”
姥姥说买季老头儿的书更上算,人家书上说的也都是咱家有的事儿,遇上解不开的疙瘩,你看看人家季老头儿是怎么说的,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姥姥在季老后面加上了个“头儿”,于是季羡林就变成了姥姥嘴里的季老头儿了。
日子久了,我们家也都跟着叫“季老头儿”,好像季老是我们村儿的一个普通老头儿,全家都叫的可顺嘴了。
姥姥看季老头儿的书多半是书里的照片,整天看、反复看。
我表妹说:“别看了,再看就看上人家了。”
姥姥也不客气:“这季老头儿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不碜(丑)的人。”
姥姥指着季老留学德国时穿着西装照的那张照片,那时候的季老确实很精神很漂亮。
我逗姥姥:“你要真看上人家,人家肯定也看不上你,人家多大的学问,人家会好几国外语,你就会写自己的名儿,不般配呀。”
姥姥不无忧伤地无数次感叹:“我就是没遇上个好社会、好家庭,没摊上个明白的爹妈(姥姥的哥哥、弟弟都念书了),要不我怎么也得念念书、上上学,弄不好我还是季老头儿的同学呢!”
我们几个听了都哈哈大笑,姥姥自个儿说完也戚戚地笑,只是笑出了泪水。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身上的血水已经没有多少了,这珍贵的泪水饱含了姥姥怎样的渴望和遗憾呀,只有我明白。
“姥姥,你不是常说一个人一个命,一个家一个活法吗?咱别老跟人家比呀,在我眼里,你没上过学照样也是个文化人,我相信,你就是季老头儿的同学。”
我急于用心擦去姥姥戚戚笑出的泪水,安抚姥姥那颗痛楚的心,极力保护姥姥那份美好的渴望。
从此,我们在家里都称呼姥姥为刘鸿卿同志,是季羡林同志的同班同学。
姥姥心里一定是为自己没读书纠结了一辈子啊。
我也劝姥姥:“读书其实也是挺苦的一件事儿,书念多了,痛苦也就多了。”
姥姥说:“这么说话的人都是自己念书得着好处了,怕人家再沾光。念书多了,知道的事儿多了觉得那是痛苦,那都是烧(烧包)的!别的咱不说,书念多了的人就比别人多活了好几辈子。念了书不用出门哪儿都去了。两条腿再能走,你这辈子能走多远?看了书你想上哪儿跟着书走就行了。”
“哎,姥姥,你没念过书怎么那么了解读书人呢?”
“咱还不会看吗?俺那场儿没念过书的那些老人岁数一大就像个傻子一样,你们这儿的人,那些电视上的干部,多大的岁数都精精神的,人家肚子里有东西,再说了,有苦也不是坏事,苦多了甜就比出来了。你吃一块儿桃酥试试,又甜又香,你再吃一斤试试?你那嘴呀就想找块咸菜往里塞。孩子,别怕苦,苦它兄弟就叫甜哪!”
姥姥没念过课本上的书,可生活中的书姥姥一直在念呀。
姥姥和季老同是山东人,年龄相差三岁,都差点活到一百岁。
然而他们走的人生之路却完全不同,日子也过得千差万别。
有一年我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在那儿遇见季老了。
回来,我跟姥姥说:“今天遇见你同学了啊!”
姥姥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是季老,因为姥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同学”。
我说:“其实季老也挺可怜的。一个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儿,这么冷的天,里外穿了四件毛衣。不好看不说,关键是多不得劲呀!有的毛衣都磨得只剩下线了。四个毛衣袖子套在一块儿,你试试,胳膊都不能打弯,季老站在主席台上两手伸着像个稻草人。再说,也不暖和呀!你看老头儿冻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一个人一个过法儿,又不是没钱,买个丝棉棉袄宽宽松松的穿上既暖和又舒服。”
转天姥姥就把我叫到屋里跟我商量,说让我去买块藏蓝色的丝绸,再买一斤二两的蚕丝棉,她说要给她同学做件棉袄。
这回我没逗她,立刻就去了当时的友谊商店,又跑了元隆绸布店,把姥姥要的东西全都买齐了。
一个星期姥姥就大针小线地给季老把棉袄赶出来了,拽断最后一根针线我就给季老送去了。
那天我还特意带去了我们山东的水疙瘩咸菜和姥姥蒸的全麦馒头,这都是季老最爱吃的。
在堆满厚书的小屋里,季老吃着馒头就着咸菜,穿着老乡给他做的丝绵袄,频频点头。
我相信老人家是激动了,我也有些心酸。
这么大的名人,这么大的学者,日子不也就这样过吗?
我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不想遭罪的人得遭一辈子罪,想遭罪的人遭半辈子罪就行了。”
季老年轻的时候就奋斗,奋斗了一辈子不也没享多少福吗?那福到底是什么?
我回来问姥姥。
“这么个过法对他可不是遭罪,人家这就是享福。罪和福一人一杆秤,对季老头儿来说,不写书、不看书就是遭罪,守着书睡觉比守着钱睡觉享福。他爱吃咸菜可不是想遭罪。”
呜,还是同学了解同学呀。
-END-
点击阅读原文或长按识别下图专家解析白蒺藜的功效与作用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ly/7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