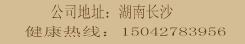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天意从来高难问路遥之平凡与传奇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天意从来高难问路遥之平凡与传奇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天意从来高难问路遥之平凡与传奇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天意从来高难问路遥之平凡与传奇
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
年4月,在路遥追悼会上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致悼词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刚刚在杂志上发表了《白鹿原》,还没有出版单行本。陕西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作家贾平凹即将出版他的《废都》;著名作家高建群已经出版了《最后一个匈奴》。文学史上著名的“陕军东征”概念虽还没有正式出炉,但已然形成了事实。此时的情形是:一方面路遥的去世给陕西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又都纷纷厚积薄发,创作出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作品。于是,陈忠实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早逝的不幸逝去,活着的还在想着文学。文学这个魔鬼啊!”
对热爱它、从事它的人而言,文学历来都有一种魔力,而对于路遥这种把文学当事业,并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来写作的人来说,文学的魔力更是超乎想象。更何况,在他驰骋文坛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正处在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和被商品化冲击之前的“黄金时代”,启蒙和教育的功能和使命尚未退却,读者的概念也更多的是“精神知音”而非“文化消费者”。换句话说,那时候的文学虽称不上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正如日中天,有能力用自己的魔力回馈作家。他们相互对待的态度都是郑重而严肃的。
实际上,在拼尽全力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早已因《人生》的广受好评、因它被吴天明改编成电影而天下闻名了。《人生》的书和电影产生的反响用“举国皆谈”和“万人空巷”来形容,绝不为过。新近出版的《路遥传》里说,以路遥当时的声名和当时的文化体制,如果他没有更高的追求,完全可以凭着《人生》一辈子安身立命。在文艺界,一本书作家、一首歌歌唱家、一幅画画家等并不鲜见,但“路遥是位心性要强且格外理性的作家”,他立志要做巴尔扎克式的“时代的书记官”,用一个“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鸿篇巨制跨越《人生》。
无独有偶,后来出版的《白鹿原》,题记用的也是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见,写出一部足以记录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当时陕西很多实力派作家的追求。不同的是,同样问鼎茅盾文学奖、市场和口碑双丰收的陈忠实只是立下了“不成功就回家养鸡”的誓言,而写作《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却为此赔上了性命。
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详细纪录了自己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所做的三年准备工作。如今看来,那无异于文学的圣徒所做的修行。除了海量的阅读,就是“在生活中的奔波”,为了准确和真实,他不放弃报纸上的每一个细节,也不忽视一棵小草和一朵小花的时令,甚至,为了准备这部书,他都放弃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标志性大会——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三年创作,更是真正的“呕心沥血”:百万字的篇幅,在爬格子的年代,即便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就是多么浩繁的工程!更何况还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呢!据他的弟弟回忆,到路遥写完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思想甚至一度不能回到现实生活中,连过马路都需要人搀扶。
路遥说:“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信念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这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猝然倒下。”“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时至今日,当我们体会《平凡的世界》长盛不衰的励志传奇时,路遥用《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本“《平凡的世界》诞生记”所纪录下的强人意志和苦行僧式的创作历程本身,以及他对文学圣徒式的崇拜和文学带给他的精神上的支撑,已然和孙少平、孙少安们融为一体了。
好在,路遥没有倒在“出师未捷”的路上,他感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3亿听众听《平凡的世界》的盛况;戴上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陕西省第一个茅盾文学奖作家的桂冠;他看到了14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他享受了巨大的声名。饶是如此,他以42岁的年华逝去的时候,有作家还是发出了“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不值得”的慨叹。因为,创作的艰辛只是这部书命途多舛的开头,出版挫折和不被文学界认可,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从主流文学界的反应来看,甚至可以说,将近30年过去了,《平凡的世界》仍然艰难地走在争取“成功”的路上……
名著诞生的必经之路
出版挫折,似乎是名著诞生的必经之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曾被退稿的名著不胜枚举。《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洛丽塔》这种先锋实验性质的文学自不必说,就连《包法利夫人》、《动物庄园》这样世俗烟火和人性人情元素充裕的作品,也因刷新时代的文学规范或者远离时代主流而被退稿。当然,在此过程中,受众心理学也发挥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名著,人们总是倾向于它拥有更多的“故事”和“花边”,而从不被认可到人尽皆知这种最富戏剧性的转变,显然最符合“名著传奇”的发展桥段。
中国当代的这几部“名著”:《尘埃落定》曾经辗转多家不得出版;《白鹿原》出版尽管未遇挫折,但编辑为此压力重重,后来为了参评茅盾文学奖而反复修改;《平凡的世界》的经历则更奇特一些。如果说,前两部作品,文学界和读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共同认定其为“中国当代纯文学的绝唱”的话,那《平凡的世界》至今还处在尴尬的状态:与巨大的市场销量和自发的读者口碑形成反差的,是主流文学界对它的“冷淡”。厚夫在《路遥传》里写:两本最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本只字未提路遥的作品,一本只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
其实,文学界对《平凡的世界》的态度,路遥生前就早就有体会。据当事人回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出来之后,时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作家路遥,曾找人交给对他有伯乐之功的大型纯文学杂志《当代》,并提出三个发表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然而,他被退稿了。终于辗转在广东的《花城》杂志发表并历经波折出版之后,曾经召开过一个专家研讨会,但“评价并不高”,据说连会后的聚餐都免了。开完会回到陕西,路遥在自己的文学导师柳青的墓前放声大哭……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以超常的意志和自信创作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当然,这两部的发表和出版也是一波三折。甚至,它荣获茅奖之后,还是有两种声音一直存在:一是它获茅盾文学奖是“运作”的结果;二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是在年,在历届茅奖中评价最低。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心性高傲、敏感多思的路遥承受了多少内心的义愤和苦难,而“以死拼得《平凡的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或许至此才显露了它真正的含义。
多年之后,《当代》杂志的主编、当年的退稿编辑周昌义仍然坚持着自己当时的判断:啰嗦、浅白、所有的故事发展都在预期之内。而且,他进一步回忆当时的文学背景:那时候的文学正被先锋的风筝诱惑着,作家们“被创新的狗咬得连撒尿的机会都没有”,路遥的现实主义显得笨拙而不合时宜,他背负的“时代书记官”的使命也被视作一厢情愿、毫无意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评价亦是如此。
《路遥传》里记载,路遥对自己与文学主流的差距不是没有感受,尤其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遭遇文学界“差评”之后,他也曾下决心要研究卡夫卡。当然,除了文学本身,路遥对文学界的人与事,也有过这样一种个性化的认识:“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
自古英雄皆寂寞,更何况是在“文无第一”的文坛呢!
《平凡的世界》的传奇
与文学界的“冷漠”相对照的,是读者的热诚。
“凡有井水处,能歌柳永词”,《平凡的世界》出版近30年来,巨大的销量已是难以计数。在多次的读者调查中,它都是最被喜欢、最被珍爱、最被感动、最被震撼、对自己影响最深、最励志的书。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前夕,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网站所做的一项读者调查研究发现: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读者最喜欢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互联网上,网友自发建立了“路遥吧”“平凡的世界吧”等等。其中百度贴吧的一项调查,更是饶有趣味。有网友发起了“有多少80后喜欢《平凡的世界》”“看这本书的90后有多少人?”的调查,结果是一万多人参与,而且,90后的比例也不低。至于每个人读《平凡的世界》的回忆文章和心理感受,更是数不胜数。无数的读者为这部书奉献了最真诚的敬意:潘石屹说自己七看《平凡的世界》,在创业之路上每遇挫折,都会看一遍。倪萍说:“看路遥的书,你觉得他不骗你。”而最近播出的电视剧的导演,更是抛开收视率的质疑,说“名著不需要浮躁和猎奇”。
一部写-年中国社会和人情的书,一部充斥了太多乡土生活和政治气息的百万字的大部头,一部风格“土气”“笨拙”的书,何以能够走进一代代读者、甚至走进对这些生活完全陌生的80后90后读者的心里?
书中的年轻人,经历着极度的苦难但保持着极度的自尊;面对着刻骨的城乡差别却拥有刻骨的爱情。或许,身处中国城市化大潮中的年轻人,都能从中发现一点生活困境和道德完善之间的撕扯,都能如孙少平一般,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或许,这些年轻人也在渴望那种“七仙女爱上穷小子”一样的纯洁浪漫的爱情,渴望成为道德完美的人格英雄;或许,这些年轻人都被书中浪漫的诗意和挺拔的精神所感动;甚至那些枯燥的乡村政治,都可以让出身乡土的年轻人感同身受;或许,读者把它当成了可以读懂的、有故事有人物的当代中国史……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读《平凡的世界》的理由。在城镇化大潮的波涛汹涌中,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轻人走出乡土走进城市的巨大历史潮流中,《平凡的世界》恰恰充当了一个精神舢板。
黑格尔说,历史有时候是以恶的形式向前发展的,然而在历史和时代之恶中,路遥说,还挺拔着强悍的人格,昂扬着奋斗的精神,充满着浪漫的诗意,保持着道德的完善。现实固然残酷,但理想依然壮美。路遥几乎是用一种火一般炙热的力量,用文学为所有苦难和奋斗中的人创造了一种“乌托邦”,而且,路遥真诚地相信这个“乌托邦”。在苦难中,他没有任何萎顿和颓靡,相反,他输送着一股强烈的能量,一股龙跳虎距般的强人人格。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路遥的灵魂配得上他的野心,也配得上他承受的苦难。
路遥的人格密码
贾平凹在《怀想路遥》里面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路遥兄弟姐妹多,幼年过继给伯父,上学后成绩优异,但因家境贫穷,只能当从家里带粮食的“半灶”住宿生。《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打饭的细节,源自路遥刻骨铭心的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路遥正要上初中,而家中已经无力供养,最后在父老乡亲的帮助下他得以进中学读书。他在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详细记录了当时的饥饿体验,甚至这种体验和当时强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以及用优异的成绩,用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学动态的阅读来平衡心理的经历等等,都让病危中的路遥念念不忘。
年,路遥考上了中专,但“文革”爆发,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无限期停止,毕业生原地闹革命。路遥的革命激情被点燃,并很快成为核心人物,被选为进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代表,后来又因为“大智大勇、敢做敢为”,被推举为学生领袖,直至最后一步步变成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接着,年来了,百万知识青年到乡村去。路遥作为老三届,也要回乡劳动。命运仿佛一心要跟想跳出农门的路遥开玩笑。他与城镇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心理波动,被融会在高加林这个经典形象里,成为《人生》这个小说所反映的重要社会维度之一。
之后,路遥还想过要当兵走出黄土地,但因为涉嫌武斗中的一桩命案而不了了之。然后,他就力图通过和北京知青的爱情改变命运,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二次终于修成正果。之后,命运总算出现了转机,路遥上了大学,并走上了创作之路,并由此站上了人生的巅峰。
然而,内心的苦难与孤独从未离开过他。生活中,路遥嗜烟如命,表情冷峻,极少言语,在别人看来,他仿佛是一个谜。有朋友回忆,路遥在文坛上没有几个关系好的人,他看得起的中国作家也没有几个;也有文章说,如果路遥活着,不知道陕西文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白鹿原》还能不能有今天的命运。据说,他的骨灰被兄弟抱离作协的时候,偌大的作协院子没有一个人来送行。《路遥传》里写,在文学作品中一团火热和赤诚的路遥,在生活中却有冷漠的一面,他对养父养母的态度令人唏嘘。而也因为他的冷漠,在他临终前三个月,在病床上签下了妻子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上个世纪80年代,知青陆续返城之后,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很多“知青小说”,路遥和两个北京知青的爱情与婚姻,某种程度上比很多小说都复杂微妙,都意味深长。
了解路遥的生平经历,会深深体会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欲望强大到什么程度,体会时代和个人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深深体会一个想要走出黄土地的年轻人在理想、欲望与现实、困境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挣扎。由此,便能够体谅他身上的野心勃勃和急功近利、体谅他的自信高傲和敏感自卑。如今看来,路遥是他那一代人中的典型,他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丰满的文学形象。或许可以说,路遥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平凡的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跟人与文的这种联系和映照密不可分。
读《路遥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路遥的哭:他经常泪流满面,对朋友哭,对兄弟哭,想女儿哭;回忆的时候哭,读作品的时候哭。连他最后住院期间的医生都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忧郁的男人。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哭,有时候倚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眼泪就滚落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里,总是会让人想到《人生》中的高加林进城失败,面对刘巧珍已经出嫁,自己重返乡土的处境的时候,那一番痛哭;也能够想到孙少平伤愈出院,看到煤矿和煤堆的时候,眼中涌出的泪水。在改变命运的路上,除了自己的泪水,什么能够表达路遥们的酸甜苦辣和百感交集呢……
面对困境,中国文化中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其中,“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的心态颇为一些人欣赏,然而路遥与生俱来的性格,密不透风的苦难让他毫无喘息之机的状态,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此。用《平凡的世界》里的话说:“是啊,这是命运!”
路遥传奇与文学的没落
客观地说,文学界说的《平凡的世界》的问题,都存在。但它里面仍有很多关于爱情和苦难的细节触动人心,也有很多人生感悟足以作为人生语录让人铭记。然而,当我们今天试图探究它真正的魅力所在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试图探究路遥之所以成为路遥的原因何在的时候,书或者“文学”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一目了然。
或许,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当孙少平和郝红梅忍着屈辱去拿“黑非洲”的时候,他们心里装的是《卓娅和舒拉》,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红岩》,是所有跟阅读和精神有关的东西。在生活的贫困之外,他们的精神无比富足——那些置身苦难中的年轻的心,并不像外人体会得那么贫瘠荒凉,相反,却是一片草木葱茏。而正因为书的滋养,他们养成了高傲的精神,可爱的气质,并以此来抵抗人生的苦难和屈辱,当然,也以此吸引城镇女孩儿的目光——哪怕这种爱情被称为“穷小子的白日梦”。
年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跟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对比阅读,探讨时代如何对待年轻人的城市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两种典型人物精神气质上的差别。同样是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同样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已经成了大学生的涂自强在生存的困境之外,却没有找到任何精神的支撑。他不断地努力,但却不断地沉沦,甚至在沉沦的路上,连爱情的抚慰都没有,直至最后寂寞毁灭。一个年轻人徒劳自强的悲伤弥漫了整个文本——文学该怎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该如何处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该怎么既洞察历史又抚慰人心,是路遥和方方两代作家提出的命题。
而读《路遥传》,更可以看出文学对路遥的支撑作用。他如饥似渴地爱着书,爱着文学。最终,也是文学真正成就了他的城市梦,成就了他的个人价值实现——当然,文学也让路遥变成了精神上的贵族,有底气、有自信去追求北京知青,哪怕这种底气和自信被人质疑为“爱情和婚姻上的投机取巧”。
如今看来,那时候的文学,确实拥有改变命运的魔力。后来,随着全面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成熟,文学逐渐边缘化,不断没落。或许,路遥在文学之路上的奋斗,在为很多普通青年励志的同时,也该为文学励志,为阅读励志。至少,该唤起一种真诚对待文学、郑重对待文学的态度和品质,让文学变的纯粹一些,再纯粹一些……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不妨将本文分享至朋友圈
如果您心中有话要说,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微社区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zz/2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