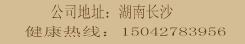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倪萍念书的人不管他长得模样,你仔细看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倪萍念书的人不管他长得模样,你仔细看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倪萍念书的人不管他长得模样,你仔细看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形状 > 倪萍念书的人不管他长得模样,你仔细看
日坠山涧,寺钟响起,
洗尽了铅华,感受夜凉如水。
在青灯烛影之中,
享受一次心灵抚摸,倾听一段动人的故事,
这里的夜,
不属于诗人,
而属于那些孤寂的灵魂。
■文|倪萍
姥姥还喜欢一个作家的书:莫言,说莫言长得和水门口村的人一模一样,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有出息?
我说莫言长得不好看,小眼睛,黑乎乎的。姥姥说没见过哪个大双眼皮的汉子好看,单眼皮筋道。
姥姥喜欢莫言是因为他实在,姥姥对莫言书的评价就是这两个字:实在。
“净说大实话,说的你听一遍就记住了。”
苦难、贫穷、饥饿在莫言的书里都写到了极致,这些文字的记忆都深深地印在了姥姥的脑子里。
好几个故事我给姥姥念的时候,姥姥也都是不停地抹眼泪。
姥姥感动的是这个和他们村里的人长得一模一样的作家,心里没有忘记这些苦难,苦难生成了一种力量,为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而努力学习,出人头地,当个写书的人。
多么真实,多么不掩饰,多么难能可贵。
理想有时候起步很小、很具体,但最终它有可能变得很伟大,有可能从为自己不自觉的变成为他人、为全人类。
姥姥最佩服这样的人。
姥姥说:“人哪,不敢穷;社会啊,不敢乱。社会一乱人就穷了,人一穷了就更乱了。莫言这孩子去念书就是想吃个饭,吃个饱饭,这叫个啥?叫志气!连个想吃好饭的志气都没有的人还能干个啥大事。”
我在家也常翻陈丹青的书,姥姥也跟着看书里的话。
我指着陈丹青的照片,“你们村可没这么好看的人吧?”早年也有,这阵真不好找,但你的意思人家长得不现代,这可是一个最时尚最前沿的人了。
不是我是说,像这么利利落落清清爽爽的男人真是不多了,旧衣服穿在现代人身上,就是好看加上好看。
你看看人家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长得一点也不糊涂,眼睛蹬得这么大,一粒沙子都进不去。
人家陈丹青最值钱的就是脑子不糊涂,我跟姥姥说。
姥姥真逗,谁的眼睛长的不是眼睛?但是我知道这是姥姥夸奖人的一个方式。
姥姥认为人的外表和他的内心一定有一处是连接的,连接点不同,做人、做事的方式也不同。
偶尔也给姥姥念上一段陈丹青的文字,姥姥的评语是:“是个有数的人”。
这路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说话有的时候像咬人一口,这路人在单位当不了大官,谁愿意整天被人咬?
姥姥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准确地计算着每一个人。
我告诉姥姥陈丹青还是个教书的先生,姥姥对他的敬重油然而生:“这路老师能教出好学生,学生不怕骂!”
姥姥指着陈丹青的照片:“念书的人不管他长得模样,你仔细看都长得好看。书念的越多,人长得越俊,没念过书的人眼神都是傻的。”
姥姥说的俊是指气质,姥姥说的傻是指没魂儿。
姥姥说得准,陈丹青是个有灵魂的人。
姥姥跟着我在书里认识了不少作家,有些作家的书我都不怎么翻了,姥姥还跟我提起他们,比如赛珍珠,她的书现在市场上都买不到了。
在很多年以前我基本上都买齐了,姥姥喜欢她也是因为她写的那些事儿,姥姥都熟悉也有感受,姥姥佩服人家,一个漂亮的外国女人在中国的农村和村民那么有感情,这就是神哪!
姥姥的评价也挺准确的,就像那个花啊,根啊、叶啊都是外国的,可是埋在咱这个地上,喝上咱浇的水,吃上咱喂的肥,长着长着就成咱这儿的花了。
你别看开的那些花还是人家原来的那个样,可是性子啊、魂儿啊慢慢地就不一样了。
姥姥说赛珍珠的内心、灵魂已经涌进中国人的圈里了,你看挺准的吧。
后来我又给姥姥读赛珍珠的传记,姥姥从传记里知道她有一个傻孩子,晚年很不幸。
姥姥挺感慨的,她该抱着孩子回中国找个中医看一看,孩子兴许能好!人家帮了咱中国人的忙,咱也该帮帮她呀!
萧红的小说姥姥也爱听,小说的语言、小说中的故事也是姥姥熟悉的。
姥姥对她的评价是:这个闺女真会写,写的那些话和北极村的那闺女写的一样,干脆利索,一听就再也忘不掉了。
姥姥说的北极村的姑娘是指迟子建。
在我还不认识迟子建的时候,我就给姥姥读过她的书,也是拣一些姥姥听得懂的章节。
比如说她写的种菜的、纪念她父亲给它做灯的那些事儿。
姥姥知道迟子建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中国最早升腾起太阳的地方,姥姥迷信的说那个地方出生的人都是神人,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个神地儿。
有一天我拿回来一张我跟迟子建合影的照片,我说姥姥你给相相面,照片上的那个人有什么神的地方没有,姥姥笑了,“一对儿神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娘肚子里生的姐俩呢”。
姥姥说我和迟子建长得像,都是神人。
因为姥姥爱听书,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一个大字不认的老太太都这么明白知识的力量,我这么个认得一些字的人还不好好读书不应该呀,于是我努力地读书,姥姥努力的听书。
“你这么说叫人笑话!”
想起有一次记者问我的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我说:“我的老师是姥姥,她教我要说人话。”我回来跟姥姥说起这事的时候,便引出了上面的那句话。
真的,我仔细的回想一下,我从第一次拿起话筒做主持人,脑子里就有姥姥的神情。
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
别觉得自己比人家高,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这是姥姥告诉我的。
在长达近20年的主持生涯中,我始终要求自己把语言打碎了,把心放平了,把文词拆开了,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话说出来,这是风格吗?
我以为是,至少这种风格合适我,念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文字也不用显摆出来,人家一看房子结实不结实,就知道你地基打得多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说姥姥是我的老师,真不是我抬举了姥姥,是姥姥抬举了我。
在做人方面,我们的下意识行为和姥姥的下意识行为真的不能比,有的时候我真怀疑是姥姥没念过书,还是我没念过书。
有一次我带姥姥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说啥也不收钱,他说倪大姐,你看难得有机会拉你一次,就让我为你服务一回吧,倪大姐。
你在电视上为我们服务了那么多年,其实就是16块钱,我们俩推来搡去的,谁也不放弃,最后还是我们姥姥接过钱,往师傅手里一放:
你这个同志,这是你的工作,哪能不收钱?要是上你家吃顿饭,你要钱我也不能给。工作归工作,你还得交单位钱,还得买汽油,你大姐挣钱比你多,你挣个钱不容易。
日后凡是遇上不收钱的司机师傅,我多半说的都是姥姥,这套话连我儿子都会了。
妈妈,你怎么每回说的都跟老奶奶说的一样,你不会换个说法。
孩子,妈真的找不到比这更实在更管用的话了。
在姥姥面前,我的语言真是太贫乏了。
还是十几年前吧,词作家曹勇回泰安给他母亲过生日,回来跟我们感慨一番。
他说我们兄弟几个这回都凑齐了,我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都动筷子了,可是我妈老往厨房跑,我寻思她干什么,就跟着进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老太太在那儿背着身从挂着纱布帘的碗柜里,拿出了一大碗冒了白泡的剩冬瓜汤,在那叽里咕噜往肚子里倒,我回身就把客厅里那一桌子菜掀了,我说咱们哥几个现在都算是能人、名人了,都算是挣了钱,有了一官半职了,可咱妈还在喝着馊了的剩汤剩饭,咱谁知道?咱谁留心过?咱妈喝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喝,我们他妈的还有脸坐在这儿喝酒。
曹勇说他连哭带骂的,把兄弟几个全都说哭了,他最后自己哭的不省人事。
回到家我就把这段跟姥姥学了,我告诉姥姥就是写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的那人,很有才情的一个作家。
他还写黄河泰山,我看他写个小沟小坎都不行,怎么就不知道他掀了这一桌子菜赶不上让他妈把这碗剩菜汤喝了?
当妈的心儿子一辈子也不知道!
么是甜,么是酸?
孩子有出息,妈喝酸奶也是甜的。
孩子更不懂,妈的肚子是铁肚子,管吃么也坏不了,就是不能吃气,吃一口气赶不上喝一口苦汤……
掀桌子,这叫么?这叫不孝啊!文化人净办些不文化的事。不过这也算是个好孩子了。
好和坏在姥姥眼里不怎么分明,有的时候我就问她,您说我算好人还是坏人?
姥姥说坏人身上有好,好人身上有坏,没有坏透了的人,也没有好得一点毛病没有的人。
姥姥绝不是混淆是非,她就是这么过的一生,这么手心手背的丈量着日子,大难担过,大福也享过,从从容容地过了九十九年。
在我的记忆里收麦子的日子是水门口的节日,那个时候家里的主劳力都上山抢麦子去了,副劳力也没闲着,晒麦子的、做饭的,家家烟囱都冒着烟,从山顶上看去,水门口像是着火了,气象万千。
院子里、村口的路边上大道上、生产队的场院里,堆得全是麦子,金色的水门口。
那几天我是村子里最闲的人了,又是村子里吃得最好的人,烙饼不断,猪肉不断。
都是沾姥爷和舅舅的光,那时候天不亮,姥姥就起来烙饼,东西两口锅全都冒着热气。
中午饭舅舅他们都在麦地里吃,我就是那个送饭的人,左手挎一个筐,里边是用毛巾盖着的发面豆腐卷子,右手托着一个陶罐,里面盛着干萝卜条炖肉。
怕饭菜凉了,我既要走得快又不能洒出一点汤。
到了麦田里,我就在树下等着队长吹哨子收工吃饭,哨子一响,麦地里呼啦啦就出现了好多人头。
我舅舅总是第一个下河沟洗手的人,第一个上来吃饭的人。
等姥爷、舅舅吃完了饭,我再跨着空篮子,托着空罐子飞快地跑回家去吃我的饭。
多金贵的饭姥姥都是提前给我盛出一碗放在锅里捂着。
收麦子的日子顿顿饭不重样。
姥姥说,人要每天都吃好饭,就得勤快点。
那为什么不天天收麦子?
好日子得分着过,光吃麦子肠子就细了。
麦子收完了,没用的闲人就开始在山地里捡剩在麦田里的麦穗了。
我自然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可那时候麦子那么金贵,收麦子的人早已经把地皮都翻一遍了,哪还有剩麦穗?
我常常是挎着个空篓子去,提溜个篓子空回来。
姥姥依然鼓励我,明天还得接着捡,捡一个姥姥也不嫌少,捡多了,姥姥就用你捡的麦子给你做个大馒头吃。
第二天我真的捡了一大篓子,这是从生产队场院的麦子垛上捡的。
我邻家的一个舅舅在场院看场,他看我挎个空篓子从那走,人家就说小外甥从那麦垛上抽一把吧,上哪捡去,地里连个麦子毛都没有。
我懵懵懂懂的知道这是生产队的东西,不能拿,可是我又懵懵懂懂地觉得拿了也没人知道,这一篓子麦穗能蒸好几个大馒头。
回到家,姥姥把我捡的麦子晒上了。
过了好几天,我问姥姥我捡的麦子怎么还没蒸上大馒头啊,姥姥从碗柜里拿出一小团生面,说这麦子也不知道咋了,怎么也发不起来,怎么也蒸不熟,我没说是在哪捡的。
又过了几天,我依然没有吃上馒头,开开碗柜,那团白面发黑了,上面布满了一层灰蒙蒙的毛绒线。
姥姥这是我从生产队的麦垛上拿的,我还挺委屈地哭着,姥姥说难怪蒸不熟,公家的东西拿回来那就叫偷,以后可不行了,偷的东西蒸不熟。
当天晚上姥姥就给我蒸了一锅大馒头,每个馒头上还用胭脂点了红点,我真的永生记住了馒头上的红点,记住了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那些少粮寡月的年月,姥姥肯浪费这么大一团面来教育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说姥姥你应该去教育部工作,姥姥说去看个大门、蒸个饭还配得上。
姥姥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
哥哥每年放暑假都来水门口看我和姥姥,姥姥的骨子里其实还是重男轻女,哥哥来住一个月,姥姥几乎不重样,给他做着吃。
有一回吃包子,哥哥把包子馅全都吃了,包子皮塞进院墙的石头缝里,一群蚂蚁向姥姥打小报告。
第二天姥姥又包了同样的包子,只是吃饭的时候哥哥的碗里光有包子馅不见皮儿。
全家人开始吃饭了,已经上小学的哥哥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他愣了一下,掀开那碗馅伸手去拿包子,姥姥把他的手打回去了,把那碗馅推到他面前。
蚂蚁说俺小外甥就爱吃馅不爱吃皮,怪姥姥不知道你习惯,从今开始,再吃包子、饺子你就单吃馅儿。
不是姥姥,我吃不了了,我把包子皮塞进墙缝里了。蚂蚁没撒谎,俺小外甥也没撒谎!
姥姥家的包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不连皮吃啊就不是那个味儿。
哥哥现在是个挺大的干部了,走到哪只要吃包子,绝对会把皮吃了,我相信哥哥终生也不再这样浪费粮食了。
前几天哥哥来北京开会,我俩还坐在餐桌上说起这事,不太爱动感情的哥哥满怀深情地说:“真想姥姥了。”
哥哥和我都记得姥姥常说的话,粮食养活你的命,你不爱惜粮食就是不爱惜你的命。
粮食是姥姥的命,早年间孩子多的,姥姥家秋粮还没下来之前就青黄不接了,人家都是去借点粮,渡过难关,姥姥从来不借。
姥姥说什么,大伙的肚子都空着,你借人家把自己的肚子填满了。
人家的肚子不是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说的都是有用的话。
姥姥的“动手”很惊人,秋玉米还没长熟、长透的时候,姥姥就掰下来煮着吃,最会算账的姥姥在别人看来这真是不会过呀。
姥姥说少收个三四十斤,明年使使劲就省出来了,孩子饿着肚子可耽误长个了,过了长骨头的年龄,这辈子也长不出了。
一家人吃着青玉米,啃着还没长大的酸苹果,等待着秋收。
如今姥姥总说共产党真是有本事,粮食不够吃了就号召大家减肥,现在是个人就减肥,一年得减出多少粮食啊!
姥姥一辈子都是吃半饱,早年是省着粮食,现在是省寿命,姥姥说人吃多了不能长寿。
-END-
点击阅读原文或长按识别下图复方白芷酊价格大概得多少哪家治白癜风的医院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zz/7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