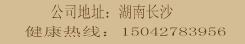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丨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丨

![]()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丨
当前位置: 猛犸象 > 猛犸象的繁衍 > 倪萍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丨
日坠山涧,寺钟响起,
洗尽了铅华,感受夜凉如水。
在青灯烛影之中,
享受一次心灵抚摸,倾听一段动人的故事,
这里的夜,
不属于诗人,
而属于那些孤寂的灵魂。
■文|倪萍
80多岁的姥姥以她的粗针大线给大文化人逢着棉袄,我相信姥姥是快乐的,是得意的。
已经多少年不做针线活儿的姥姥手戴着顶针,眼睛上戴着眼镜,穿针引线依然是那么娴熟。
“就像你们骑自行车,打小学会了,现在你就是会开飞机了,你再骑自行车也没说不会骑的。”姥姥说。
姥姥对季老的关心还是源于我。
15年前写《日子》,那时候季老曾经开玩笑:“人家倪萍现在也是作家了。”
我真的是脸红,《日子》不过是一堆废话,季老竟说他也要一本。
我心里其实还真想送去,我那时候问姥姥了“你说这合适吗?和季老的书相比,咱这真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书啊。”
姥姥说:“要书不丢人,给书也不丢人。没听说哪个大人不让小孩子说话,有时候小孩子能说出一堆大人的话。”
姥姥和我都清楚,季老写的是大书,我写的是小书。
硬着头皮给季老送去了一本《日子》。
再去季老家的时候,李阿姨说,《日子》叫他家的一个亲戚拿走了,季老还催着要回来,说这是人家倪萍送我的书,书不可以被人拿走。
我很感动,大人尊重小孩。
以后的又一年,季老回山东老家官庄给他母亲上坟,我带着摄制组跟机采访,顺便也把三岁的儿子带上了,读好书,交高人嘛。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一路上季老都看着窗外,偶尔看看车厢里的人,逗逗孩子,话不多却很温情。
你如果不认识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地道的乡下老头儿。
我和平静的季老面对面的坐着,平时挺能说的我此时却不知道该说啥,我也看着窗外,偶尔看看季老、看看孩子。
我坚信那天季老内心是翻江倒海,你想嘛,快90的老人了,心里揣着年轻的母亲,那滋味你去体会去吧!
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不在了,儿孙也不在,回家看谁呀?
可季老依然是那么急切地往家奔,一上午的慢车在季老来说就像是在坐飞机,心早已去了官庄。
我一路也在盼着。
离县城只有30公里的官庄是个挺大的村子,村子里有多户人家。
有电视的人那时候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还是黑白电视,于是我在那儿出现,就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县里来的干部。
官庄以盛产大蒜而出名,那里的蒜个儿个大、肉香,家家门口的院子里都像拍电影一样,挂着一排排的“大辫子”优质蒜,有一个老乡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一个劲地追着我问:“你们要不要大蒜,五毛钱一大辫子,要多少都有多少……”
我那时候要有车真想拉回一车,不是需要,而是真的想成全官庄这位老乡的这笔“生意”,多好的大蒜。
官庄人的质朴让我感动。
8月6号是季老出生的日子,那天清晨我们摄制组是和太阳一起走进官庄的,我们想赶在季老回官庄给他父母上坟之前先拍拍官庄。
可是一进官庄我们知道来晚了,因为官庄那天家家户户都起得特别早,六点多钟,好多孩子妇女都已经聚集在街头了。
村庄的街道被他们打扫得一尘不染,虽说是土路、土房子,可你竟然会觉得这是乡亲们用乡情为季老铺下一块最松软、最好看的红地毯。
我被感动了。
更让你感动的是村里许多人不知道季羡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更不知道它如今的身份是什么,它对中国的贡献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他是官庄人。
上午8点季老回家了,“家”里有上千人在村口等着他,年长的、年少的都往前挤着想看看这个“奇怪”的官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真没什么两样,一件旧的的确良白衬衫里套着一件圆领汗衫,一条绸子裤好像因为洗的次数太多了,都泛白了,而且在脚脖子之上,太短了。
这就是人们在这里等候许久的“家”里人吗?这么一个普通的小老头。
季老不停地握着每个人的手,嘴里说着什么你也听不清楚,但是你从他那平静的脸上还是能看出:季老激动了,因为到家了。
季老带着从芝加哥回来的孙子季泓在此爹娘坟前长跪不起,那一刻,原本像开了锅一样的官庄安静了,小孩子们不懂事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人们懂事是因为这一刻谁都理解了普天下最容易懂得的一种情感,谁没有爹娘,谁没有儿女,谁没经历过生离死别……
一个满肚子文化的人,和官庄最普通的百姓一样,给爹妈的坟前摆上了点心、水果,还有鸡鸭鱼肉。
我相信此时此刻躺在坟里的两位老人一定是心满意足了,他们的儿子在他90岁的时候还回来看望父母,这不也是父母最知足的事吗?
回到北京,我们又把季老请到了台里的演播厅,做了一期谈话节目《聊天》。
季老很少上电视,那个时候电视上谈话节目也很少,季老给我足够的面子了。
我们说了很多小事,家事。
我读过季老写的一篇散文《永久的悔》,读了很多遍,每次读的时候,那种痛的感觉永远新鲜。
我们山东有句老话,说:“儿子长得特别像妈”,所以我问季老:“你长得像你母亲吗?”
没想到季老说:“不知道!我母亲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一张照片都没有?”
“没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能有照片?”
季老在书里写道:“我在母亲身边只呆到六岁,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那天我还特意请来了濮存昕,朗诵了一段季老的《永久的悔》。
朗诵结束,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我当时真的有一种愿望,真想告慰已经长眠在官庄的、季老的母亲,她用尽所有的想象都不可能想到,自己养育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孩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季老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看了播出的这期节目,姥姥说:“人哪,该干啥的就得去干啥,季老头儿会写书不会说话,坐那儿像要睡着了。”
从官庄回来,姥姥急于知道季老的故乡行怎么样。
我就详详细细地把官庄那几天的日子全都向姥姥汇报了。
我说:“你看季老母亲的命真够不好的,才不到50岁就死了。”
姥姥却说:“人家这个妈真是有福啊,死了比活着好。”
“姥姥,天下哪有你这样的理,什么叫死了比活着好?”
“你想啊,有儿不能见,家就一个孤老婆子还算个家吗?活着就是受罪呀!”
季老说他母亲长得什么样他都记不清了,模模糊糊记得六岁他离开家去济南那天他母亲是倚在门框上的,日后母亲留在他记忆中永远就是这个画面。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再没见到母亲,直到回来为他母亲奔丧!
他说见到母亲棺材停在门厅的那一瞬间,他恨不得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而去。
如果还有来世,他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呆在母亲身边,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种个田地。
悔呀!
那几天姥姥为季老长吁短叹。
我问姥姥,如果你是季老的母亲,你有这么一个儿子,让你去选择,你是送他出去读书,还是留他在身边种地?
姥姥脱口而出:“送去读书呀!天下有两个妈,一个是大妈,一个是小妈。孩子也有两个,有干大事的孩子,也有干小事的孩子。季老头儿的妈是个大妈,孩子也是个干大事的孩子,必定得是送去。”
姥姥说的大是伟大,伟大的母亲用更远大的母爱把孩子舍出去为天下做事,不管你自己情不情愿,不管你自己多么辛苦。
季老的母亲完全可以从官庄去济南把孩子领回来呀,即使不领回来也可以常常去看看啊。
从官庄回来我们不再和姥姥开玩笑了,也不再叫她是季老的同学了。
我们一家对季老的尊敬中又多了一份心疼,姥姥也多了一份牵挂,牵挂季老的母亲。
现如今,季老、姥姥都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人生又重新开始了。
假如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以重生,我盼望姥姥真的能成为季羡林的同学。
我坚信姥姥一定会选择读书认字,成为一名学者。
我也坚信季老会带上他的母亲去种地,娶上媳妇、生上孩子。
“盼望、盼望,盼多了、望多了,你那个盼望就能实现了。”这是姥姥常说的话。
在宽大的书架前翻着一本厚厚的书,是姥姥在我们家常有的画面。
起初你想笑,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手捧一本满是字的书看什么?
慢慢地你就有些心酸,她一定是渴望知道这书里都写啥了。
再后来你就想哭,想到姥姥每次拿起书差不多都会说一句:“哎,睁眼瞎,长个眼好弄么?”
不认字又喜欢字的姥姥真是痛苦啊!
“这个世界上不认字的人多了,人家不都过得挺好的?”
“他要是摸着心说实话,没有一个敢说他过得好。不识字,多闷得慌。”
闷得慌,姥姥的心闷得慌。
我不忍心让姥姥闷得慌,所以我常给姥姥念书。
张洁写的那个《母亲的厨房》刚上市,我就买回家念给姥姥听,书很薄,几天就念完了。
姥姥说:“写书也不是个多大的事,你看人家也没写个啥,就是过日子那点油盐酱醋,烙个油饼炒个菜。”
“哈,老太太,就这才不好写呢!平凡的日子人家写的让你那么爱看,这就是大家。”
又过了一阵子,姥姥拿着张洁写的另一本书《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你给我念念这本书吧,这上面写了些啥?”
“老太太认字啊,这不是那个张洁写的吗?”
哦,姥姥认识书里的照片,两本书里都是同一个女人。
这本书被姥姥催得基本上是一口气读下来的。
今天你只要停下,姥姥明天一大早就起来就问:“医院回来了吗?医生怎么说?她那个外甥书包从美国来电话了吗?”
好多地方姥姥都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我说:“姥姥,你看你这么难受,咱就别念了吧?”
可是姥姥每次都说:“念吧念吧,我不是难受,我这是好受。”
姥姥说的“好受”我懂,她从张洁的这本书里享受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情、母女情。
张洁在书里说:“一个人在54岁的时候成了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
姥姥听了这话又哭了,姥姥说:“你告诉张洁,妈早晚是得走的,妈走了闺女还能活,知足吧。要是闺女走了,当妈的可就活不了了,一辈儿一辈儿的都是这样。”
莫不是姥姥又想起他的小儿子了?她在50多岁的时候失去了20多岁的儿子,她不也活过来了吗?
姥姥说:“我都死了几回了,只有我自己知道……”
家是什么?家里的人是个什么关系?不就是这么琐琐碎碎地忙来忙去吗?
你搀我一下,我扶你一把,似乎今天过得跟昨天一样。
一样的日子有人过得有滋有味,有人过得麻木不仁。
姥姥崇尚苦日子一家人搅拌着过,“不好吃的菜一人一勺就见盘子底儿了,好吃的馒头越蒸越香,越吃越有”。
姥姥这样评价张洁这本书:“说的是家家都有的事儿,可是人家说的你就那么爱听,听了还想听。”
听完了这本书,姥姥对张洁娘俩的牵挂不亚于她们的亲人。
那年春节,乡下的舅妈送来了一筐大铁锅蒸的新麦子面的开花馒头,一个就有二斤重,大个的都像脸盆子那么大。
姥姥非让我给张洁送去两个。
我笑了,我虽然多年前采访过张洁老师,也认识,但北京不是你们水门口啊,说上人家家提溜着两个大馒头就去敲门,吓着谁。
姥姥真的不明白,认识的人怎么还不能来往?
“别看馒头不值啥钱,可在北京有钱也买不到。”
我知道姥姥绝不是因为张洁没了母亲怕她吃不上饭,姥姥的内心是觉得自己有个大的不能再大的热水袋,灌满了她的善良,谁需要谁就可以拿去暖和暖和。
热水袋凉了可以随时换上热水,没有热水了还可以放在怀里加加温。
热水袋不值钱,但却管大用,因为有爱。
姥姥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爱,这种爱铺设在亲情、友情之下,是一个社会上最基本的温暖,是一种自然的相互帮助、相互给予,是人性里最天然的东西。
姥姥说:“这样你上哪儿去都不用担心,见了谁也不用害怕,就像在自己家里。”姥姥盼着社会是个大家庭。
姥姥还牵挂一个人,史铁生,也是因为听了他的《我与地坛》而认识的。
这个我已经给姥姥读过几次的散文,姥姥也那么喜欢。
姥姥心疼这个“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突然残废了双腿”、“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这样想了好几年”的孩子,姥姥舍不得这个“一下就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的孩子”,姥姥更舍不得那个“一辈子心就倒下了”的史铁生的母亲。
“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
可不是吗?
史铁生的妈妈40多岁就去世了。
姥姥说“史铁生这妈是挺不住了,跑了”。
“不该想不通啊,得这么想:还有赶不上咱孩子的,人家的妈不都挺着?这就是心没倒,心没倒就活得起。这路孩子更得有个妈,没有了妈,孩子就等于又少了一个胳膊。”
姥姥预言史铁生能活个大岁数,“别看这孩子遭点罪,一个星期换三回血,死不了。他妈用命给他换着寿哪”。
与其说这是姥姥迷信,不如说是姥姥是美好祝愿。
我答应姥姥,有机会见到史铁生,一定把这话传达给他。
直到如今,我也没见着史铁生,他太低调了,只让书露面。
他每一个版本的书我都买,即使重复了,我也买齐。
我和姥姥买他的书就是为他的生命加油!
姥姥也是在书上认识贾平凹的。
我跟姥姥说政协开会,我们俩在大会堂的座位是紧挨着的。
姥姥觉得我真了不起,净和一些有能耐的人坐在一块儿。
在姥姥眼里,能写会画的人都是有能耐的人,特别是那些农村出来的文人,姥姥更是高看一眼。
姥姥说:“趴在炕上能把字写周正的人,你不让他去念书那真是白瞎了。从前农村有个啥?灯也没有,桌子也没有,连张写字的纸都没有,还能出个写书的孩子,那不就是个神吗?”贾平凹是神。
长大了我才明白,为什么穷的时候,姥姥家一年中吃的最好的饭是学校的教书先生派饭的那几顿。
一堆像破布一样散散的油饼被姥姥用好几层毛巾盖着,那香味隔着院墙就能闻到。
大铁锅旺火炒的茄子丝,葱花爆炒的白菜心儿,那真是香啊!
-END-
点击阅读原文或长按识别下图北京治疗白癜风费多少钱北京中科白癜风双节惠民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ly/644.html